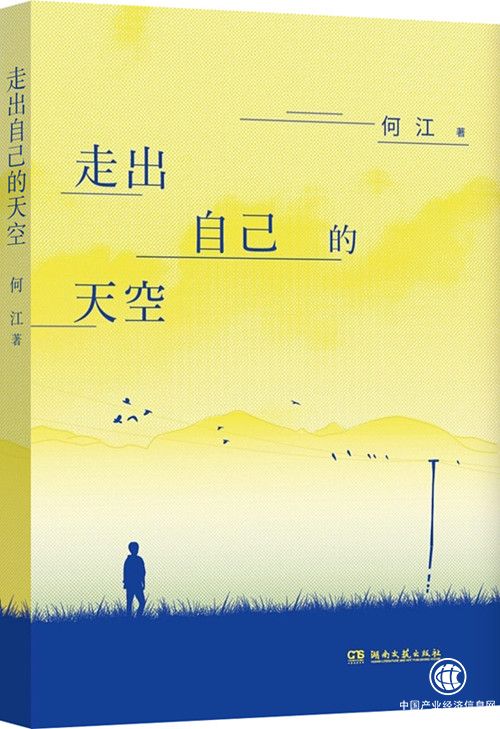成為歷史上第一位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演講的中國人之后,何江出名了。他從一個貧困的中國農村走來,通過教育改變人生軌跡,走進世界最頂尖的學府,正是人們熱衷于追捧和討論的故事。
然而,在最新出版的自傳《走出自己的天空》中,何江并沒有如眾人所料去描繪一個成功學的故事,而是將筆觸落在他所成長的中國農村,記錄正在發生快速更迭的鄉村舊生活。鄉村如何造就他,他又如何書寫鄉村?記者在近期落幕的上海書展上采訪了何江。
澎湃新聞:自從你的畢業演講發表以后,媒體做了很多報道,甚至到你的家鄉,采訪了你的家人、老師、鄰居。你覺得自己的經歷是因為什么樣的原因吸引了公眾的高度關注?
何江:當時我沒想到會傳播這么廣。過一段時間回過頭來看,我想可能是“農村學子”和“哈佛”這兩個詞的碰撞使人們產生了關心。很多人還是很難把這兩個詞聯系到一起,這激起了他們了解背后故事的欲望。媒體問得最多的問題還是圍繞我的成長和教育經歷,并且熱衷于討論教育公平、“寒門貴子”這些話題。
澎湃新聞:你曾經介紹過,最早對你的經歷表示出濃厚興趣的其實是美國人,是哈佛大學的教授尼爾·弗格森,能分享一下他和你交流的內容嗎?
何江:五六年前弗格森教授在哈佛做了一次關于經濟全球化的演講,特別提到中國這幾十年在經濟上的崛起。但他們看到的數據是大層面的,對底層的鮮活事例了解得比較少。演講后我與他交流,他了解到我的求學背景,表示很感興趣。
我是1988年出生的,那時候湖南鄉村仍然保留了非常傳統的農作方式,后來慢慢引入機械化、自動化農作方式,這在一個歷史學家眼里就是一個快進版的、歐洲的工業革命,中國在三十年內上演了西方國家上百年經歷的歷程,正是這個對話觸動了我寫這本書的想法。
澎湃新聞:你是在什么時候意識到,這段經歷似乎處在某個特別的歷史進程當中?
何江:我和弗格森教授聊過天以后又過了一段時間,才隱約感覺到。其實是需要和自己曾經生活的世界拉開一段距離,在美國生活了一段時間以后,遠觀之下才逐漸有這些感受。寫這本書花了三、四年的時間,中間來回修改了很多次。當時還沒有畢業演講這回事。
澎湃新聞:在《走出自己的天空中》,你對大眾最關心的“成功故事”似乎沒有著墨太多,而是記敘了很多童年回憶,寫你的村莊,寫你做織漁網工的母親、捕魚的父親、你的弟弟,村里的老房子、烏江河……為什么選擇以這樣的方式來寫自傳?
何江:我其實并不完全把這本書定義為我的自傳,這是我個人對鄉村經歷的一個總結。我最開始寫書的時候很多人認為我應該寫一個勵志故事,但我自己比較抵觸這種方式。雖然雞湯有時候會溫暖人心,但讀者看完不會從中得到真的收獲。如果大家好奇我怎么從農村一路走到哈佛、麻省理工,那大概需要真正地了解,我的家庭是什么樣的,我當時求學的經歷是如何,我所處的村莊、成長環境是什么樣的。
我認為每個人的道路是無法復制的,每個人會有很獨特的人生經歷。大概只有通過白描式的書寫,才能更好地表達一個人的成長,同時也許能夠帶給別人一點靈感。
澎湃新聞:那你如何選擇你所描繪的對象呢?
何江:最開始其實不知道該用怎樣的方式來寫這本書,后來是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才確定下來。第一章“假如春天能夠留住”就是直抒胸臆地,把我從出生到哈佛的歷程寫下來,是一個白描式的回顧,這是我的成長軌跡。然后是我和身邊親人交流對話的過程,我的父母、弟弟就自然而然地就進入到書寫的視野中去。常常有人問我我的家庭教育是什么樣的,其實看了這一段就知道了。比如我的父母沒有外出打工,我和弟弟沒有成為留守兒童,父母給我們講外面的事,伴我們讀書,這些其實對我的成長有很大的影響。從自我,到家庭,再推而廣之到我所生活的村莊,我寫“秋天的訪客”,寫“盛開生命的房子”,其實就是寫更大范圍的一個成長環境。
何江筆下“盛開生命的房子”。勇斗銀環蛇的母親、把蜈蚣拍成肉醬的父親、在老鼠洞前犯愁的自己、駝背的算命先生……這座老房子里有他念念不忘的童年回憶。
澎湃新聞:你透露了很多關于家庭的細節,是否和家人商量過?
何江:寫到父母親人的部分,我都會把初稿給他們看,請他們來閱讀、反饋,并且跟他們求證確認一些細節。盧梭寫《懺悔錄》,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真,只要是他的感受和經歷,好的壞的都寫,我寫作的時候也受到這個影響。沒有細節的話我感覺不真誠。
澎湃新聞:除了盧梭,對你影響比較大的人文社科閱讀有哪些?寫這本書還受到誰的影響?
何江:海明威,梭羅,陀思妥耶夫斯基,何偉。這本書受海明威的《流動的盛宴》、何偉的《江城》影響最大。人文社科方面的閱讀有《萬歷十五年》、《人類簡史》、《槍炮、病菌與鋼鐵》、《自私的基因》、《局外人》等等。
澎湃新聞:你最喜歡書中哪一個部分?
何江:我個人最喜歡第四章,“盛開生命的房子”。這章寫的是我小時候生活的老房子,通過它可以看到我小時候成長的環境。那看起來是個很清貧簡單的房子,卻有很美好的回憶,那是單調的城市生活很難獲得的樂趣。
澎湃新聞:在你的書中我讀到很多富有傳奇色彩的描述,比如家人用蜘蛛治療蜈蚣咬傷“以毒攻毒”,比如養了一條蛇在家里抓老鼠,吃飯的時候蛇就懸在房梁上,還有現實版的“守株待兔”,吃田鼠、挖黃鱔以及村里的巫師、捕蛇者等等,這些鄉村圖景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
何江:現在農村土磚房變成樓房以后,房梁上掛著蛇的情況也再不會出現了。像抓田鼠、黃鱔和挖泥鰍這些都是美好的童年回憶,現在城市里長大的孩子很難和大自然有親密的接觸,不太會經歷類似的事情。
其實寫這本書的很大的動力,就是看到傳統的農業社會在逐漸消逝。我小的時候農民是拉著水牛犁田,拿著鐮刀割水稻,現在則是靠收割機。傳統的手工農業勞作的方式,在我們這一代消逝了。幾千年前來的文化基因,很有可能在新世紀里就沒有了。我希望能把它們以我自己的方式記錄下來,這是我希望這本書能承載的記憶。
澎湃新聞:你在書中寫到村里的現狀,說很多農民變成了農民工,離鄉背井跑到城市打工,卻又請人打理家里的一畝三分地。你怎么理解這樣的做法?
何江:這是現在這個大變遷時代的必然現象,其實這是工業革命的翻版,傳統社會的人走向工業社會,在城市里還沒能完全立足,但又對鄉土有很強的依賴,有一種土地情結吧。
澎湃新聞:你在書里寫到算命先生和巫師,有一處說:“一個巫師退隱了,村里又會有不同的人借著一些鬼怪之事宣揚自己具有異于常人的法力——只要有人信,就會有人干。”你怎么看待這些不會輕易消亡,仿佛有無盡生命力的傳統?
何江:我寫這句話的時候,其實心里對鄉土、對傳統是有一種很復雜的情感。現代化的浪潮在滾滾前進,傳統的很多東西在我們這一代逐漸消逝,但它們又有很頑強的生命力,仍然在鄉土,在農村根深蒂固地存在。很難說好不好,很多人向往都市的生活狀態,但傳統的文化鄉土的文化同樣具有它的魅力。這大概也是所謂“快進版的工業革命”中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
澎湃新聞:你在書里還說,父母雖然沒有受過很高的教育,但是相信知識改變命運,村里的小孩要走出鄉村,最快捷的方式便是讀書。這些年村里的觀念、教育有沒有變化?
何江:我父母即便教育水平不像城市里的人那么高,他們對“知識改變命運”這一點還是認同的。現在有些地方又開始討論“讀書無用論”,這的確是一個現象,資源比較少的地方的人想通過教育突圍,成功的比例越來越小。父母看到辛苦培養的大學生掙錢還不如打工的人掙得多,產生懷疑也很自然。在我的家鄉其實大部分人還是堅信教育的力量。但有些地方我知道不是這樣的觀念。
澎湃新聞:自從你被媒體發現以后,“農村”的標簽就再也沒有摘掉過。你怎么看待一提到你就要講農村背景這件事?
何江:我認為對任何一個人都不應該用標簽去定義他。一個人應該首先認知自己作為一個獨立的存在。只有認清楚自己的價值,才不會被這個標簽所局限。可能很多人會因為“農村”、“哈佛”這樣的標簽而忽略我的本職工作其實是生物科研,但又有人以為科研人員只會埋頭研究。但其實每個人都有一些獨特的成長經歷。我自己其實不太介意身上的標簽,只要我自己心里對自己有不同的認知就可以了。
澎湃新聞:你的畢業演講講的是改變科技與知識分布不均的問題,那在你將來的規劃當中,對于改變鄉村和科技知識的傳播有什么樣的規劃嗎?
何江:我在演講中說,希望高深的科技知識得到更廣泛的運用,我去麻省理工讀博士后,其實就是在做這方面的嘗試。麻省理工就是偏實際應用的學校。我現在做的研究,也更貼近這個目標,是有關肝臟移植、人造肝臟、研究新藥治療乙肝、瘧疾,以及癌癥早期的檢測。相較于在哈佛時期的研究,其實就是把課本和實驗室里的東西應用到生活中去,讓更廣泛地區的人能夠受益于這些科學研究。目前的高新技術往往集中在像波士頓這樣的大城市,我想我在做的就是改變這種現狀的一個嘗試和努力。
版權及免責聲明:凡本網所屬版權作品,轉載時須獲得授權并注明來源“中國產業經濟信息網”,違者本網將保留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的權力。凡轉載文章,不代表本網觀點和立場。版權事宜請聯系:010-65363056。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