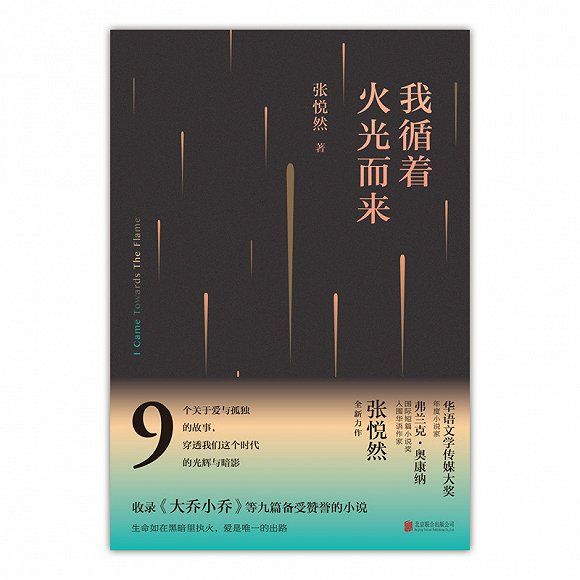繼長篇小說《繭》之后,張悅然日前又推出了一本短篇小說集《我循著火光而來》。在新書的連線發布會上,臺灣作家張大春提到了張悅然很多作品都有“雙生花”的意向,即兩個女性之間的關系。文學評論家楊慶祥也認為,張悅然小說最擅長的,是寫一對看起來很親密的兩個姑娘之間的關系。對此,張悅然回應說,對她來說,女性之間是一種鏡像關系,通過另一個人可以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處境,因此,需要這樣一個可以作為鏡像的女性存在。
《我循著火光而來》收錄了張悅然近8年來的9部短篇和中篇作品,她塑造了許多彼此之間隔膜頗深的主人公,他們很難靠近,但又存在著某種幻想,使得他們仍然渴望接近他人。雖然很多時候,他們最終會被火光灼傷,但這種靠近的努力本身,幫助他們對抗了生命的虛無和無意義。
在發布會現場,《收獲》雜志主編程永新提到,張悅然十多年來一直努力寫作,期間也發生了一些改變。從早期創作幻想小說,到近些年來轉而關注生活、取材現實,“從現實的縫隙中尋找想象和虛構的可能”。這是我們剖析張悅然寫作路徑的角度之一,然而其變與不變還有更多維度的內容。
蘇童(左)、張悅然(中)、楊慶祥(右)對談現場
從信馬由韁想象,到向現實交出霸權
2001年,張悅然參加第三屆新概念作文大賽并獲得一等獎。在2003年到2006年間,她共出版了六部作品,比如講述兩個從小到大一起成長的女孩如何化敵為友、如何面對友情、愛情和生死的《櫻桃之遠》,比如充滿了青春文學橋段的《水仙已乘鯉魚去》。同年,張悅然發表了充滿瑰麗想象的長篇作品《誓鳥》,講了大航海時代的一名中國女子遠下南洋的故事。她被海嘯奪去記憶,流落荒島,經歷生育、病痛、牢獄之災,她刺瞎雙目,只為尋回失去的遺跡。
直到2016年,距離上一部小說出版十年后,張悅然終于交出了自己的第二部長篇小說《繭》。這一次,張悅然從空中樓閣般的華麗想象轉向歷史,轉向了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張悅然曾在多個場合談到這本小說的創作契機。《繭》源于她的父親寫于1978年的一篇名叫《釘子》的小說。在父親當時住的醫院大院里,一位叔叔在政治運動中遭人迫害,變成了植物人。張悅然曾反復聽父親講述這個故事,于是決定把它重新寫下來,變成自己的小說。張悅然回到那個醫院,通過工作人員找到了一份植物人檔案。其中記錄著此人出生、參軍、退伍、工作的時間,直到他的腦袋被摁入釘子。這份檔案成為了張悅然《繭》的開始,而《繭》則成了張悅然直面父輩、追尋歷史的開始。
《繭》
張悅然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8月
《我循著火光而來》中一篇備受關注的小說是《大喬小喬》,于今年2月首次發表在《收獲》雜志上。不同于《繭》對于父輩經歷的追尋,《大喬小喬》開始直面屬于八零一代的獨特記憶。故事的主角是正常出生的姐姐與意外存活的妹妹,后者是因患有心臟病而無法實施流產手術的母親在引產后生下的二胎,姐妹二人因性格與命運的不同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張悅然將主人公放置在宏大的歷史和時代背景中,計劃生育、階級、權力等等因素,在這個故事中輪番登場。
在程永新看來,張悅然沒有受到“80后作家”這一標簽的左右,她有著自己的判斷和堅持,“能夠將世界和中國當代優秀的作家視為參照物,謀求寫作的上升通道”。從早期的幻想小說《誓鳥》,到最新小說集中收錄的《嫁衣》、《大喬小喬》以及《動物形狀的煙火》,他認為張悅然已開始直面當下生活。而在將真實的生活材料轉變為文學素材的時候,作者其實是面臨考驗的。他將這樣的小說看作“從現實的縫隙中尋找想象和虛構的可能”,生活素材與虛構于是構成了一種限制和反限制的關系。
2008年汶川地震后那段奔赴四川做志愿者的經歷,對張悅然的創作產生了直接的影響,促使她寫出了小說《家》。男女主人公想要逃離原來的生活,于是來到四川震區。在張悅然看來,小說中的主人公陷入了生活的無意義,因此想通過幫助他人完成自救。她在接受采訪時說,《家》是自己寫作上的重要轉折,意味著“從耽于幻想轉向關注現實”。
張悅然說,在她之前的寫作里,更多的是一種空中樓閣式的想象力,是一種“說它是它就是,說它存在它就存在”的作家霸權。但當她了解更多現實之后,她的小說便需要和現實發生更深層的關系,小說作者此時“失去了霸權,需要去遵循現實中的規則,按照現實中的邏輯來規劃小說”。張悅然也坦言,這個過程對她來說比對其他很多作家要更難一些,因為她之前那種信馬由韁的想象力使用得比較過度甚至是泛濫,所以回到這條現實的軌跡上異常辛苦。
《我循著火光而來》
張悅然著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10月
“一個有良知的優秀作家,就是要把直接來源于生活的元素和素材轉化為虛構,”程永新認為,“如果小說的任務僅僅是把生活表達出來,那跟新聞報道有什么區別。作家為什么要去虛構?就是試圖挖掘人性當中最隱秘的部分,就是要講當代人的精神,就是要讓作品擁有某種深度的東西。”在寫作的過程中,張悅然一直在尋找現實與虛構之間的張力和維度,比如關注超生問題和社會公平等等。在當下這個資訊發達甚至過剩的社會中,“作家存在的價值在于眼光,就在于處理如此繁多的材料時的態度,在于如何處理虛構與現實的關系”,程永新說。
相較于階級差異,更關心個體困境
隨著年齡增長,張悅然覺得自己變得慈悲了,變得溫暖和有所保留。這種性情的轉變也影響到了她的寫作,“年輕時候的寫作更加絕對、尖銳,也會更加冷酷,因為不能夠真正看到或者理解到悲劇真實發生的情況”。她說《動物形狀的煙火》里好像還有很尖銳的部分,但到了《大喬小喬》則有了更多溫暖與包容。
今天的張悅然更想“以小說寫那些被自己的努力過程改變的人,而不是那些被某個結果改變的人”。她希望自己小說的主人公去做出嘗試,不斷爭取更好的改變,比如嘗試和某個人靠近、去打破某種僵局、去承擔以前不能承擔的任務。即便這些嘗試最終失敗了,它們也是有意義的。“我更看重徒勞的過程加注在主人公身上的意義,更多的時候,人們被這樣的過程所改變和影響。”張悅然說。
也正因此,她并不輕易給故事主人公貼上失敗者的標簽,她認為自己所寫的并非是失敗,而是一些困境中的人物。比如小說《家》里那對因空虛和生活無望而出走的夫妻,以及受困于原生家庭的保姆——對寫作者而言,這些人物所面臨的困境是難以進行比較的。
張悅然認為,短篇或中篇小說里沒有徹底的解決方法,只有一種短暫的重歸平靜,或者說問題暫時得到了某種緩解。因此對她而言,短篇小說的結尾更像是:主人公遭遇了一些事情,現在需要重新面對和思考原來的生活或問題,即重新上路,或是重新帶著一個議題回到最初的人生道路上。“在小說里面,我常常會讓人物去做這樣的努力,這個努力使他明白:好吧,一切都沒有意義,所以做這個努力是對抗無意義的唯一途徑或方式。”她說。
曾有文學評論家指出張悅然這部小說集所涉及的階級和社會階層議題,但張悅然認為,人所經歷的真實的困境與痛苦才是她的關切,而非階級的差異:“不能因為我寫的人物不是底層人物,或者不是那些被物欲損害的人,他們的痛苦就會更小一些或更不急迫。我們要知道,那些痛苦可能同樣是使他們活不下去、使他們出逃的痛苦。”
在小說《家》中,張悅然產生了一種模糊的認識,得出了一則在之后的創作中反復提到的結論——只關心那些對主人公來說急迫的,現在必須面對、不面對就活不下去的痛苦——不關心主人公究竟是一位億萬富翁,還是一名乞丐。
文學評論家楊慶祥認為,除了小說寫作本身,《我循著火光而來》還展現了張悅然作為作家的自我意識和自我身份的變化。如果系統地閱讀這部小說,“可以窺見張悅然從早期風格開始慢慢的向更加成熟、更加理智的方向轉變,能夠做出的一些自我調整和自我表達”,張悅然的寫作“在自我氣質上不停地生長展開,慢慢長出一個更茂密的森林”。
承襲張愛玲的冷酷,塑造“雙生花”的意向
與這些變化形成對照的,是張悅然作品的不變之處,比如對于女性間情感的細膩描寫。在早期作品《櫻桃之遠》中,她便塑造了兩個相伴相生的女孩;在《大喬小喬》這一從超生話題展開的故事中,她再次用細膩的筆調描寫了一對姐妹。
在連線對話中,張大春認為張悅然對女性之間情感的描寫非常珍貴,“張悅然直接承襲了張愛玲的冷酷”。張大春說,張愛玲雖被譽為當代描寫男歡女愛的祖師奶奶,實際上非常惡毒,無論是《半生緣》還是《紅玫瑰白玫瑰》,都是從女性視角出發的、對男性的一種剝奪。而張悅然不僅把男性剝開了,還延伸了張愛玲的部分,因為張悅然的很多小說都涉及到了“雙生花”的意向,即兩個女性之間的關系。
楊慶祥也注意到了這點,他說,張悅然小說最擅長的,是寫一對看起來很親密的同性——兩個姑娘——之間的關系。
張悅然回應道,對她來說,“女性之間有一種鏡像的關系,通過對方可以看到自己,看到自己深處的處境,無論是和男性的關系、和社會的關系、和世界的關系,都需要這樣一個女性的存在。”
張悅然坦言:“有時候我構思小說的時候里面一開始只有一個女孩,并沒有另外一個女孩。慢慢地,我就會發現,另外一個女孩會慢慢在故事里面浮現出來,會變成一個像幽靈一樣的角色,就像我現在坐在臺上,左顧右盼地尋找某種東西,直到另外一個女孩在底下朝我招了招手,我忽然之間就感到安心。我需要找到觀眾席里面的某一雙眼睛,當我的主人公看到她的時候,主人公的心就定下來了。有時候,兩個女孩并不是在最初的構想里就存在著一種相愛相殺的簡單關系,而是另外一個女孩承擔起了某種敘事責任或意義,她在幫助這個故事往前推動,走向最后的結局。”(傅適野)
轉自:界面新聞
版權及免責聲明:凡本網所屬版權作品,轉載時須獲得授權并注明來源“中國產業經濟信息網”,違者本網將保留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的權力。凡轉載文章,不代表本網觀點和立場。版權事宜請聯系:010-65363056。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