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文章學”發微
——《文心雕龍》的架構與學理
作者:趙昌平 (上海古籍出版社原總編輯)
編者按
近百年來,學界基本是以西學的眼光來剪裁和評騭中國古代文學的。其結果,不是造成削足適履的難堪,便是留下隔靴搔癢的遺憾,甚至弄出買櫝還珠的笑話。魯迅先生在《葉紫作〈豐收〉序》中感嘆道:“《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嘗在羅貫中下,然而留學生漫天塞地以來,這部書就好像不永久,不偉大了。偉大也要有人懂。”不僅小說如此,詩歌、戲曲同樣如此,文章尤其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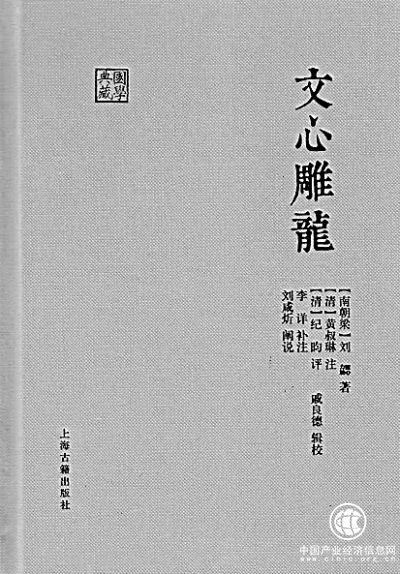
《文心雕龍》 資料圖片
中國古代許多文章根本裝不進西方“散文”這個筐子,中國許多古代文章家的藝術感覺極為細膩,神、韻、理、氣、澀、峭、趣等審美范疇,又大多在西方散文理論視野之外,用西方的散文理論分析中國古代文章,不出現方枘圓鑿那才是奇跡。汲取中國古代文章學智慧,重構中國當代文章學,以中國話語談論中國文章,是當今中國學人應有的學術擔當。
這里的三篇文章皆闡述中國古代的文章學,三位作者皆是這一領域的學術名家或學術新秀。趙昌平先生從《文心雕龍》的構架和學理入手,論析中古文章學的理論體系,要言不煩又切中肯綮。此處“文章學”相當于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此處的“文章”兼容六朝的“文”“筆”。熊禮匯先生精細地辨析了三個關鍵詞的內涵與外延,此文的“文章學”則屬于狹義。余祖坤先生論及古代駢、散和八股文評點的價值與開發,而恰如我們沒有保護好自己的歷史古跡一樣,學界至今仍舊冷落了祖傳的文章評點。(戴建業)
中古文章學,是以文章為研究本位的文學理論體系。其發生、發展經歷了由漢魏以迄中唐約600年,而《文心雕龍》則集前代之大成,開唐人之法門,堪為其典范之作。本文擬由是書之總體架構與學理著手,闡明“文章學”并無待當世學者去重新建構,而是早在一千五六百年前業已完成了具有語言批評性質的、體大思深的民族性文學理論體系。
“圣賢書辭,總稱文章”(《情采》),可見以“文章學”指稱劉彥和的體系是合其本意的。一般認為是書上篇二十五篇為文體論,下篇二十五篇為創作論,卻鮮有對其上下篇及各子篇相互關系的論析。值得注意的是后序性質的《序志》對全書架構的提示。
《序志》稱上篇為“綱領”,下篇為“毛目”。綱舉目張,可知下篇所論創作思維與為文“要術”(文要、文術)一系于上篇所論以《原道》《征圣》《宗經》為淵藪,以《正緯》《辨騷》為正變樞紐的二十二類文體之流變。這與摯虞《文章流別集》及《序》、昭明《文選》之文體分類,表現出一致的時代傾向。由此,一個初步的判斷是:此書是一種合文體流別史與文章學原理于一體的大著作,而絕不只是“寫作指南”之屬。最能說明這一性質的是與《原道》等三篇遙應的《時序》《物色》二篇的性質與位置。所謂“創作論”,其實止于下篇自《神思》至《總術》一十九篇。《時序》領《物色》,緊接其后,是關合下篇創作論與上篇文體流別論的“接榫”。這可由創作論十九篇各自的理論要點及內在聯系悟得。
《神思》居下篇之首,為創作總論,不僅揭示了文學創作“神與物游”的思維特征,更重要的是以“神思”——心神之作用為關鍵,發展了傳統文論“言、象、意”關系這一核心命題。所謂“心總要術”,“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實而難巧”,說的是心居主位將引發創作沖動的心、物之主客對待,轉化為主體內在的志氣與辭令的虛實互攝。這一點成為貫穿創作論以下各篇的紅線,故是篇總結“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謂:在積學、酌理、研閱、馴致基礎上,“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文學創作的實質就是心體這位大匠,以其玄解、獨照的功夫,妙用兼具聲象的言辭以呈象達意的“密則無間”之過程。《神思》贊云“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應。刻鏤聲律,萌芽比興。結慮司契,垂帷制勝”,正是對以上理路的概括。
心為主體雖同,但文章風格各異,故以《體性》置《神思》后加以闡發,其最重要的理論創獲是對莊子“成心”概念的改造。彥和所謂“成心”,是指區別于人人皆有的“心”體(共相),而因人以異的性情化的性心(異相),它由各人先天的稟賦“才”(智質)、“氣”(氣質)與后天的“學”(文化傳承)、“習”(時風熏陶)結合而成;文章雖風格有別(八體),而究其實,無非是“各師成心(性),其異如面”。這就將普遍性的“神思”,提升至個性化創作的境地,是對傳統的“言為心聲”說的重大發展。《序志》以“摛神性”來提挈二篇關系,其中實包含了彥和新論的兩個最重要的理論支點:個性化與對語言形式的重視。
八體有殊,然其通則是“會通合數,得其環中”,以下《風骨》篇即論此義。“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練于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可見風骨固以“務盈守氣”為本,然而氣又必待端直準確的言語方能得到駿爽的抒發。“風清”與“骨峻”上承“意”與“辭”關系而深化之,同樣是虛實互攝的一個問題之兩個方面。
風格之體又必須附麗于一定的文體方能呈現,故復次之以《通變》《定勢》,將風格之體關合于文體之體,從而由創作主體的維度,打通了創作思維(目)與文體流變(綱)的關系。“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因此能文者雖或“總群勢,通奇正”,“隨時而適用”,但“镕范所擬,各有司匠,雖無嚴郛,難得逾越”,所以作者的每一次創作,一方面是“因情立體,即體成勢”,另一方面則在“循體以成勢”的同時“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即主于成心的即時作用“隨變而立功”。故《定勢》贊以“因利騁節,情采自凝”來概括之;而《序志》在“摛神性”后,繼云“圖風勢,苞會通”,更提挈了以上各篇關系。
特定的“情采”自凝于某一文體,即生成具體文章(今稱文本),以下《情采》《熔裁》即承上申論這一“括情理,矯揉文采”的過程,而其“蹊要所司,職在熔裁”。“規范本體謂之熔,剪裁浮詞謂之裁。”此本體,注家多謂指思想內容,然上文云“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可知本指情理(情之理路),體指文體。雖云“因情立體”,但本與體未必絲絲入扣,故須“變通以趨時”,通于傳統而變于當時,且由成心之妙用“熔”情入“范”(文體),按部就班,是為“情理設位”。這一過程同樣是通過“文采行于其中”并加以剪裁呈現的。由此彥和將傳統的“言志”說,提升為“情經辭緯”說,去緯無以言經,故在反對“為文造情”的同時,充分強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于情性”,可見文本之情理與辭彩的關系是意辭互攝的創作活動的最終體現。
以上自《神思》至《熔裁》七篇即“心總要術”之要(文要),術系于要,故《熔裁》又下啟《聲律》至《指瑕》九篇,以“望今制奇”而“參古定法”為要旨,論各種文術之運用務必得中合度而體要,是即《序志》所謂“閱聲字”;更以《養氣》《附會》《總術》三篇總束之以呼應論文要七篇。如此總而分,分而合,系統地闡釋了文學創作以成心為主體,將心物對待的創作沖動(直覺)轉化為個性化的意辭互攝以呈象見意的語言活動,并終于產生“三十輻共一轂”、情采彪炳的文本這一內在理路。這一文本因此似“驥足雖駿,纆牽忌長,以萬分一累,且廢千里”,是一個牽一發動全身而苞情含風的語言組織,這不能不令人想起英國人貝爾關于作品是一個“有意味的形式”的命題。20世紀中葉,境內學界受蘇聯清算形式主義的影響,普遍以“形式主義”貶稱六朝文學,可稱是“歪打正著”。
然而彥和心目中意辭互攝的文章,雖具有相對的自足性,卻更在兩個維度上具有開放性,從而體現出中古文章學語言形式批評的民族性格。《序志》將作者“割情析采,籠圈條貫”的功夫歸納為“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后,即接云“崇替于《時序》”,而《時序》領《物色》,二篇正居創作論十九篇后。這樣就呼應上篇,將作者以成心為主體的語言活動置于縱向的文體(文風落實于文體)崇替與橫向的時代風會之交匯點上(《物色》下《才略》《知音》《程器》三篇為有感而發的余論,性質近乎批評論,此不贅)。《時序》稱“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說的是文章十代九變,因于世情之變化(時變)而呈現為一種演進序列,而《物色》更進一步發明作者“情往似贈,興來如答”之特定情境下的個性化創作,正是“文變”“崇替”的原動力。所謂“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為功,物色盡而意有余者,曉會通也”,揭明了一種事實:無論自覺與否,主于成心的作者的創作活動,都是對文體的因乎時、染乎世的承中有革,這是彥和文學史觀的核心。而參以《體性》所說“才有天資,學慎始習,斫梓染絲,功在初化”觀之,就認識論而言,實與當代發生認識論暗合。作者童年時的習學會影響其最初的創作傾向(認識圖式),它一方面對其一生有不可磨滅的影響,另一方面,因其處于傳統與時風的交匯點上,而在情境化的創作中,自覺不自覺地參與了會通古今,異代接武,參伍因革的文學之世變,自然也積漸地改變著原初的創作傾向。這種觀念,不僅為我們提供了考察作家文風演變的著眼點,更為解答學術界聚訟既久的“外部因素如何轉化為文本內涵”問題提供了答案。這種轉化的中介,就是“成心”。作者通過學、習,將諸多外部因素(可總稱為一時之文化)融入其先天稟賦的才(智質)、氣(氣質),使之化為成心的有機成分——已被才氣個性化的有機成分,是為前創作階段的潛識與潛能;一旦物我相擊,某種潛識被外物喚醒,潛能則通過意辭互攝,個性化情境化的語言活動做成文章:這樣外部文化諸因素便自然轉化為作品個性化的內涵了。
以上無論是“語言形式批評”“發生認識論”,都用了“暗合”一詞,這是說研讀《文心雕龍》可以二者為參照,而彥和以上新論的切實的學理背景是對傳統學術的“通變”。兼為儒家五經、道家三玄之首的《易》學,是漢魏以降的顯學,而王弼注《易》,更開啟了《易》學由重象數向重義理的轉化。筆者認為以《系辭傳》為代表的易學的思辨形態可以用這樣一組范疇來概括:中(道)——時——勢——經權與通變。人對于不可言喻的中道的把握,其實是因時審勢而得其度,從而執經用權,通于古而變于今,是為通變。《文心雕龍》通貫全書的“望今制奇”而“參古定法”紅線,無疑是《易傳》思維形態的文學表現。
與此相應,魏晉以降,何晏崇本舉末說代替“崇本黜末”說成為本體論的主流認識,而郭象馭物得中合度而不過當即為順物之天性說,葛洪學習有以砥礪人的天性說等等,則又對《易傳》人可參與天地造化及道與術數之關系的思想作出了重大發揮,從而在以上思維形態的基礎上形成了一種新的自然觀:萬物分殊理一,所謂順應自然,并非絕圣去知,而是各具成心的具體的人的心之理與具體的物之理的密合無際。《神思》篇以“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冠于心匠意辭互攝的創作語言活動之前,正是以上時代性儒道互補的新思維的反映。而當時各文化部類的細分化研究,尤其是文字學、音韻學、文體學的長足發展,更為以上新自然觀率先在文學領域催生《文心雕龍》這樣劃時代的理論著作作出了鋪墊。
至此可悟,被視為全書總綱的《原道》《征圣》《宗經》三篇,并不能說明彥和一稟儒家立場。細讀文本,三篇并非對儒家教義的闡發,而只是視六經為二十二類文體之淵源,并標示一種雅麗的語言傳統,作為“望今制奇”而“參古定法”之典范,三篇下接《正緯》《辨騷》為文章樞紐,正可見以上理路。
《光明日報》( 2017年08月21日 13版)
版權及免責聲明:凡本網所屬版權作品,轉載時須獲得授權并注明來源“中國產業經濟信息網”,違者本網將保留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的權力。凡轉載文章,不代表本網觀點和立場。版權事宜請聯系:010-65363056。
延伸閱讀

版權所有:中國產業經濟信息網京ICP備11041399號-2京公網安備11010502003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