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瓊·佩斯(Saint-John Perse,1887年5月31日-1975年9月20日),法國詩人和劇作家。他于196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獲獎原因為“由于他高超的飛越與豐盈的想像,表達了一種關于目前這個時代之富于意象的沉思”。
昨天我在等飛機的過程中,我帶了一本叫做《數學頌》的書,這是一個剛剛出版的新書,作者阿蘭·巴迪歐,當代法國思想家在中國最有名的一個。他研究生命哲學,在他的哲學體系里有四個重要的支柱,他認為這構成人類哲學意義上的真理。一個是科學,講的是人類理性真理;一個是藝術和文學,講的是感性的真理;一個是政治,講的是集體的真理、群體真理,最后一個是愛,是講的個體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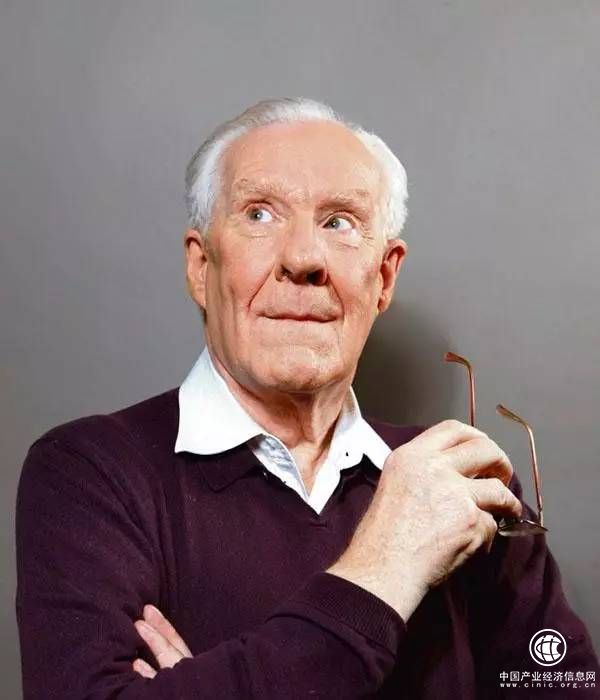
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1937年1月17日—),法國作家、哲學家。受過數學和心理學的訓練,關注哲學、政治及現實問題,前巴黎高等師范學校哲學系主任、教授,現任瑞士的歐洲研究院(EGS)教授。
這讓我想起這個杜牧的一句詩:鑿破蒼苔地,偷他一片天。那意思就是我在樹林里挖一個坑,然后讓雨水下到坑里,雨停了以后水就變成鏡子了,我就把天空從天上偷下來,所以叫“偷他一片天”。德國的一個漢學家也是我的翻譯者叫顧彬,他寫過一個專著是通過杜牧來了解中國古人的自然觀和詩歌觀。有一個當代德國大哲學家,他讀了顧彬的書和剛才我說杜牧這兩句詩以后,他就發明了一個學說叫“真實,始于二”。就“一”不構成真實,一定要“二”。要有“二”構成一個真實。而中國人講的是天地人是一個“三”,三生萬物。
但是西方人在這里面看到的是一個“自”。西方沒有“自”這個詞,到現在都沒有,但是他們自戀這個詞的一個基本的詞根是什么呢?
水仙花的英文是Narcissus,自戀的英文是Narcissism。
“Narcissus”,納西塞斯,這是一個神話人物,一個希臘美少年。有一天他去喝水,偶然在一片安靜的水面上看到自己的美貌,他不能相信世界有這么美的一個美男子,那這就是他自己,他就在那看啊看,不忍離去,最后跳到水里淹死了,變成了一朵水仙花。所以這也是英文單詞中“自戀”的一個詞根。西方通過水看到的不是天,看到的是他自己,是自我。而在中國古畫里面的人永遠是小人,沒有真正的面孔,像螞蟻那么小,人非常謙虛,人都從大自然的構成的天地關系中退出,躲起來沒有面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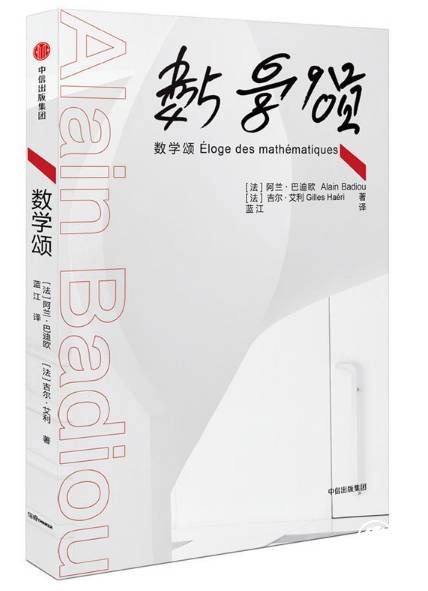
《數學頌》阿蘭·巴迪歐, 吉爾·艾利著;藍江譯,中信出版社,2017年05月,法國著名哲學家、知識分子阿蘭·巴迪歐講述數學之美,從輕松的對話中體驗思想的樂趣。
昨天我在看這本《數學頌》的時候,阿蘭·巴迪歐認為,我們當代人都不關心哲學,哲學病了,也導致數學病了,數學變成少數精英的話題、變成高深的命題,變成誰都不懂的語言,變得跟我們的生活跟哲學毫無關系。反過來講,哲學把數學驅逐出去讓它變成科學的一種,數字構成的東西跟詞語和語言沒關系,這是哲學的原罪。而按照柏拉圖的說法,哲學與數學起源于幾何學。而且古希臘意義上的數學是兩個,一個是關于空間的就是幾何,另一個是你有幾何,你就會有數字,會有邊長、角度,這些都是數字。所以一開始希臘的數學就是兩個方向:數字和空間構型,而這一切構成哲學的最原始的基礎。所以柏拉圖在柏拉圖學院里面有一句話叫做:不懂幾何學的人不準進入這座房子。其實它就是一個招牌,指的是不懂數學人別進入哲學圈。但是我們當代哲學已經變成政治話語,好像哲學和數學再也沒有關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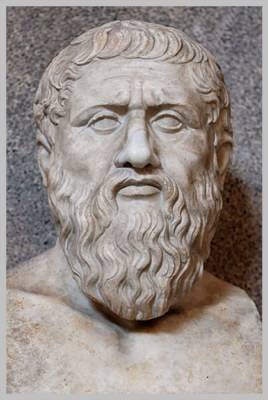
柏拉圖(Plato,Πλ?τeων, 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古希臘偉大的哲學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學乃至整個西方文化最偉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和老師蘇格拉底,學生亞里士多德并稱為希臘三賢。
自從法國把數學應試化、變成一些口訣以后,這是數學最大的遺憾,把數學變成一種非常讓人討厭的應試哲學,變成錄取某種人員的一個篩選的標準。因為數學作為一種存在方式,它完全是以存在方式的角度來理解數學。
那么數學的另一個極端是什么呢?詩歌。所以這里面要涉及到詩歌。
詩歌語言是最具有個人特征、最具有個人特殊性的語言。我們不能說詩歌語言是中文英文法文中間的任何一種語言,它當然也不是數學語言。它是一種最具有特殊性的,在無語里面也需要翻譯的語言。這是詩歌語言的一個定義,它只是在載體上要借助英語、中文這樣不同的語言來寫,但是它所表達的指向的東西,卻不是人人都能明白。詩歌的語言的特殊性、它的經驗性、它的情感性、它的神秘感,甚至它最樸素的意義上的簡單性,都包含一種跟新聞完全不同的,像密碼一樣的東西。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消費的時代,我們需要通過閱讀、通過寫作把我們的經驗變成碎片,就是和人的總體性與我們的歷史記憶和我們生命的連貫性完全脫離開來的一種碎片,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特別重要的特征。我們老是不停的看電話,看短信看微信,我們每過幾分鐘就被打斷,然后我們每天早上起來看到不同的不好的新聞報道,老是被這種東西打擾,所以我們形不成我們對世界、對自己作為人的一個總體的連續性的一個看法。我們形不成思想,我們更多的意見變成了容易被改變的簡單的看法。

活動現場
我們老是在被不同的新聞事件牽著我們的鼻子走,我們的情感,我們的思想都變成這種反應,因此我們構成不了我們整體性,構成不了宗教情感,構成不了真正意義上的對祖國對國家的記憶,對無語的認識,構成不了真正意義上的詩意。因為這一切的后面都有一個詩意的支撐,那么我們脫離跟詩歌的關系以后,我們的存在方式,我們存在的質量,我們的理解,我們的記憶,包括我們所使用的整理我們自己塑造我們自己的語言,都變質了。所以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我一直認為詩歌,尤其是我今天特別要講的就長詩是一個特別好的解毒劑。
我們這么優美的語言,被李白、杜甫、李商隱、李賀、屈原、莊子、老子、韓愈這樣的偉大的文學家和詩人寫過的語言,在我們的當代生活,我們對媒體的反應,我們所謂的正義感和激烈的情緒、我們的眼淚、我們的悲傷、我們的狂喜里面都找不到我所說的這個偉大的中文漢語的痕跡。所以我覺得一方面要恢復這種古老的鄉愁一樣的,語言的源遠流長的文化標記、文化身份、文化記憶,就像我們人從哪里來、我們是誰一樣;另一方面我們又要活在當下,活在剛才我所說的各種各樣不同的新聞媒體的碎片的環繞包圍和真實的刺激之下,然后意識到這兩者的不協調,然后我們用我們的閱讀寫作來平衡、中和、接受這種不協調,然后把他轉換為我們對生命的理解,轉化為我們對我們自己的命運和塑造,而這個轉換很重要。

活動現場
我認為,我自己的寫作,我的長詩寫作在參與到這個具有時代特征,但是又忠于中文和漢語這種優美語言的歷史的身份和記憶的轉換中間。一方面我要承認,我必須承認我一點都不討厭和厭惡,作為當代人,我還享受我們的糟糕,享受我們的碎片,享受我們的不協調。沒有關系,享受疼痛和黑暗沒問題,只要你有轉換能力,通過寫、通過讀、甚至通過不寫不讀,做好準備來接受這一切,然后把自己當成一個當代人。

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意大利維羅拉大學美學教授,并于巴黎國際哲學學院教授哲學。
我為什么在這里面要提到是當代而不是現代?因為當代和現代有一個特別重要的區別。當代不是說僅僅是“當下”這一個瞬間,當代可以是一個很古老的時刻。按照阿甘本——意大利的當代學者,他也是剛才我提到的阿蘭·巴迪歐的粉絲,是他在意大利的思想代理人,他和阿蘭·巴迪歐一樣偉大。他寫過一篇文章叫做《何謂當代》(也譯作《何為當代人》,是阿甘本在威尼斯IUAV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2006-2007年理論哲學課程中正式講座的文本內容),是寫當代美術的。他是一個哲學家,他從哲學的角度來理解當代。因為我們都在談當代藝術,但是當代是什么?當代在英文里面沒有被認真界定,它不像現代。現代經過康德最早提出啟蒙,他寫過一個《何謂啟蒙》這篇文章,小小一篇。文章提出了“現代性”這個概念。現代就是一個有明確的時間指向的概念,作為一個切割和割裂,把現在和從現在開始,人要作為一個新人,一個被啟蒙過的人,我要跟我的過去,舊我、舊時代、舊事務、舊思想、舊的生活方式,做一個切割,一個告別,像癌癥一樣把它切割掉,像闌尾炎一樣割掉扔掉。然后從現在開始我走向未來。

康德Immanuel Kant(漢譯:伊曼紐爾·康德),日耳曼人,作家,1724年4月22日生于哥尼斯堡,1804年2月12日逝,年79歲。德國哲學家、天文學家,星云說的創立者之一,德國古典哲學的創始人,德國古典美學的奠定者。他被認為是對現代歐洲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啟蒙運動最后一位主要哲學家和集大成者。
康德這里面提出了一個時間觀。到了現代主義詩人波德萊爾,變成了一個特別重要的意識形態,就是現代主義的最正式的成立。到了柏格森,他更是做了一個哲學上的總結,然后由此誕生了現代主義文學,比如說像意識流的誕生等等,都是跟這個現代性有關。他以哲學的意識形態在存在方式上界定了“現在”這個概念,以“現在”這個概念的時間觀作為一整套風格的哲學的文學的價值觀的規定,名副其實,而且行之有效,最后變成一整套技術性的東西。如果沒有“現代性”和“現代”這兩個概念的切割和因此形成的“從現在到未來”這個單向度的價值觀,那么就不會有我們的現代社會。

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 - 1941),法國哲學家,文筆優美,思想富于吸引力,于1927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夏爾·皮埃爾·波德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法國十九世紀最著名的現代派詩人,象征派詩歌先驅,代表作有《惡之花》。
“現代性”已經被證明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整套的價值觀。但是為什么我現在要提到當代詩歌?為什么我要提到當代性?因為“現代性”在這個形成了規律,藝術音樂文學政治經濟軍事都有一整套價值觀的時代,在經歷了偉大的文學、文化和中華文明的努力之后,我覺得它變得有點兒問題,越來越西方化。而且由于舊事物不合以往時代的文物考古學的時間線的任何一種,導致了時代切割之后有問題,就是我們怎么面對我們的文化遺產,文明意義上我們怎么理解,比如說杜甫身上的當代性。
杜甫身上沒有現代性,但是有當代性,杜甫的詩歌處理了安史之亂,他的處理他的反應,他對生活經驗的處理,對他身邊日常生活、日常性的處理,把日常性和那個大時代的歷史重疊在一起,然后用詩來構成詩歌最偉大的玄想和形體結構,他的努力是一種當代工具,所以杜甫在這個意義上講是一個了不起的當代詩人,而李白不是。

歐陽江河
李白是一個無時間性的時代詩人,他是神派下來的人,他不處理像安史之亂這樣的歷史問題,他對這個問題不敏感,他沒有當代性。這兩個偉大的詩人,這兩個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他們放在全人類也是最偉大的詩人。如果我們按照現代主義詩學來理解文學、理解詩歌的話,這兩個人都是過時的。但是如果按照詩歌與當代性的這個標準把他們放進去,我們就會覺得這兩個是不會過時的。大家都知道,我們閱讀古代的偉大的詩歌并不是古代詩歌在我們內心復活和被喚醒,而是反過來,是我們將我們自己對文學、對詩歌的熱愛和理解,我們的天賦,甚至我們把我們自己的經驗、我們對生命的感受,我們把這一切通過閱讀李白杜甫的詩投射到他們的影子上去、回聲中去,是我們自我在李白和杜甫的影子當中的投射。

這張照片獲得了2017年度Olive Cotton Award人像攝影獎冠軍。作品名為《Maternal Line 2017》,作者Justine Varga。
而當代也不是后現代,后現代是在有了現代之后才有的,而當代應該是前現代,和現代毫無關系。所以我們在理解當代的時候,它不是一個純粹的時間的觀念,而且還有一點:當代跟古老的事物不做切割,而是混為一談、融為一體。而且當代還有一個迷人的地方,就是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當代,它不像現代。現代是趨于一體化、趨于細分化,經濟上趨于市場經濟,政治上趨向于民主政治。現代有一整套的價值體系,政治的經濟的文學的統一體系。當代藝術跟現代藝術截然不同,當代文學與現代文學也不一樣。現代文學和詩歌是一個精英主義的東西,是出現大師的東西。而當代藝術出現了很多不完美的東西,甚至反藝術的東西都可以被納入當代藝術。當代藝術通常是不完整的、有殘缺的,反美的、崇尚丑的,或者是崇尚缺陷的、未完成的、批判性的、有活力的。這樣一些東西在當代藝術里面作為一種重要的元素,是得到推崇的。所以當代的所有的這些特征在我們對當代詩歌的閱讀寫作中是全都存在的。所以這是當代,是一些正在發聲的東西,但是早就發生和完成了,但是又在你的身上,在我們的影子里重新被喚起,重新被投射這樣一種東西。

雕塑《米哈伊·愛明內斯庫》
在這里我要重復講一下長詩。長詩里帶有我個人的一些體驗和實踐在里面。我用長詩寫作來干好幾件事情。第一,我保持中文寫作、漢語寫作的古已有之的復雜性和難懂,難以被稀釋掉,難以被消費掉的這樣一種性質。這就像前不久我特別崇拜的一個俄羅斯鋼琴家,現在住在法國,叫做格里戈里·索科洛夫。他在萊比錫的一場音樂會,里面演奏了三首莫扎特的小小的奏鳴曲以及兩首很長的貝多芬的奏鳴曲。在演出開始之前在他就講,說聽我的音樂,一定得做好準備。我有責任帶領那些做好準備來聽我的音樂的人,我有我有責任帶領他們進入我的這個音樂世界,因為我的這個音樂世界是貝多芬和莫扎特他們的世界。他演奏的是莫扎特最簡單的晚期作品,和貝多芬最復雜的晚期作品,《作品90號》和最后一首《作品111號》。這是我最熱愛的貝多芬的奏鳴曲,特別神秘。然后這首奏鳴曲的第二樂章被認為具有爵士音樂的一些特征,但是太復雜了,高深的不得了,只剩下音樂作為原理的骨頭的東西,沒有皮膚,沒有肉,沒有血液,沒有鮮活的東西,純粹是骨骸,是死亡的東西,非常了不起。

格里戈里·索科洛夫(Grigory·Lipmanovich·Sokolov·Lipmanovich,1950.4.18—)出生于俄羅斯,列寧格勒。12歲第一次在莫斯科參加大型演奏會。16歲因參加1966年的柴可夫斯基國際鋼琴大賽而聞名于世界。
他說,我彈這首音樂之前,你們得準備好,準備好你們的思想的勞動力、理解力、想象力,和特別重要的,你們身上的安靜。而安靜,真正的安靜是特別特別累的。你們聽一場音樂會,你們會聽的淚流滿面,大汗淋漓,聽的站都站不起來,因為費盡你們的心力。他說,我的音樂不是給那些上班上一整天后來聽音樂放松一下的人的,這種人我勸你把票賣掉。我的音樂,我引領人們進入的那個世界,那是一個宇宙。貝多芬的音樂世界,尤其他的晚期作品里面放了一個宇宙觀進去,一個建構,一個思想的、音樂的、人類認知的、心靈的、精神的腳手架。他放了那樣一個東西進去,你們得來攀這腳手架,你們的腳沒有落地,你們的頭懸在空中。他簡單地說一句他要引領他們,我也在想是不是我的長詩里面也有這樣的東西在里面
我聽過切利比達奇,一個羅馬尼亞的指揮家,他是非常偉大的指揮家,他一生堅決不錄音樂。他認為他的音樂是進入,通過聲音進入,不是消除聲音,就像通過自我進行自我泯滅的這樣一種高級體驗。在你死了200年以后,準許你在考古學的意義上復活那么一個小時兩個小時來聽音樂,作為一個亡靈來聽他的音樂。我去聽過一次他的《布魯克納》那真是太偉大了,聽得我目瞪口呆,我三天之內不想聽任何聲音。整個被他開耳了。

謝爾蓋·切利比達奇(Sergiu·Celibidache,1912年6月28日-1996年8月14日),羅馬尼亞指揮家,二十世紀世界著名指揮大師之一。
這樣一種東西在詩歌音樂哲學數學的深處是存在的,證明我們人不是枉來世界一趟,證明我們人類有一些特別高級的東西,特別神秘的偉大的東西,他在詩歌深處等著我們,這不是宗教,但是比宗教還要厲害的東西。他事關我們的理解力,事關語言本身是如何誕生、被塑造出來,事關你是誰。它絕不說一個人是誰,它絕不說只是一個肉體的誕生,絕不只是說你叫什么名字,長多高學歷多少,長什么樣子,穿什么衣服——當然這些構成了你自我,但是還有一種構成就是語言作為存在,你的理解力、你閱讀寫作的過程中對世界的理解、對生命的理解,由這些東西共同構成。而這些東西作為密碼在音樂和詩歌里面是存在的,如果我們不去破解這個密碼,我覺得我們有點可惜,浪費了生命給你的一些能量和一些可能性。所以這也是我為什么一直在強調,我們真正閱讀詩歌,不要去管他懂不懂,糾結于一句話兩句話、像數學一加一等于二那樣懂是沒有意義的。
比如我在讀魯米的詩的時候,他是13世紀的波斯神秘主義詩人,是蘇菲教的教主,同時是特別偉大的詩人。在讀他的詩的時候,我透過他的簡單性,正如有時候我們讀比如保羅策蘭的詩,讀荷爾德林的詩,透過他的復雜性,他的神秘感,他的不交流,因為詩歌有一個特別重要的一個特質,甚至是一個定義,就是不交流,他不是交流的產物。

魯米,全名是莫拉維·賈拉魯丁·魯米(Molana Jalaluddin Rumi)。神秘主義詩人,1252年創立蘇菲教。
我們透過這一切,透過復雜、透過神秘、透過不可知、透過簡單、透過親切、透過書籍和美,我們在認知我們自己,我們在進入一種狀態。詩歌是一種狀態,真正喚醒這種狀態的是我們每一個人,不管你是否寫詩,這個狀態都在你身上存在。就像一朵花盛開,不管我們有沒有看見這朵花,可能這朵花在兩千公里之外,也許這朵花在兩千年之前開,也許這朵花在另一個星球上開的,但是不管我們有沒有看到它、摘下它、是不是聞到了它的味道,它都是香的。詩歌所保留的人的生命的狀態,這個狀態里面包含了我們每一個讀這首詩和沒讀過這首詩的人的人生的狀態都在里面,不管有沒有文化。就像李白的詩,不管你有沒有讀過他的詩,不管你有沒有記住,沒關系,他都包含了我們對詩歌、對語言中文的基本理解,他構成我們的記憶,構成“我”作為一個中文使用者——“我” 的偉大——以及我的母語的偉大,構成這一切。李白我說一首詩作為例子:
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
上有無花之古樹,下有傷心之春草。
我向秦人問路歧,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
古道連綿走西京,紫闕落日浮云生。
正當今夕斷腸處,黃鸝愁絕不忍聽。
——《灞陵行送別》
也許這首詩你沒讀過,但是我一讀起,難道你覺得你我能夠幸免嗎?你能夠說你與詩歌沒關系嗎?凡是使用中文的人,哪怕你兩千年三千年以后使用都沒關系,你都被李白的語言塑造了。你使用的漢語被李白使用,他構成你的記憶,哪怕你根本沒讀他的書,他構成你的身份。作為一個中文使用者,哪怕你所學的語言是計算機語言,是醫學語言,都沒關系。詩就像花香一樣, 你沒有嗅它,可是花照樣是香的。所以我說詩歌內部最根本的不是懂不懂、你喜不喜歡,這都沒關系,而是它喚起了這種狀態,作為密碼、作為沒有被觸碰過的開關、作為黑暗和疼痛,哪怕作為愚蠢和麻木,但它被保留在詩歌的詩意的公共性后面,哪怕它是被少數人、甚至一個人、甚至半神的語言來形容,這都沒關系。我們要從這個意義上理解詩歌。

《長詩集》本書收入歐陽江河具有代表性的短詩精品,以及他產生廣泛影響的長詩多篇。更有最新創作的新作。具有不可替代性。
那么長詩,我的長詩集最后一首詩叫做《古今相接》,那么這首詩是特別復雜的一首詩,比我的早期的《懸棺》還要復雜。《懸棺》是我83年寫的,就已經非常復雜了。但《古今相接》,我是盡可能的不復雜,我使用特別簡單的原生態的語言。但是由于這樣,我的詩里面有很多原生態的東西。從各自的進入語言之前的原生態,到通過詞語的媒介進入到敘述、理解、保存和記憶以及表現之前原生態的過程,我想把它保留下來。所以這首《古今相接》,前前后后涉及了差不多兩百多篇讀書筆記、思考、散步的筆記以及寫作的片言只語,表面上看來特別碎片化,但是我構成了一個整體,然后又允許這些碎片作為他們的原生態存在。
而這些原生態,比如說他們在進入到這首詩之前是各種各樣不同的原生態,就像《春秋》,春秋又有《左氏春秋》、《呂氏春秋》、《不修春秋》,也有《史記》等,這些就是歷史的構成。中國的歷史大家知道有很多文學和詩歌的成分在里面,也有翻譯的東西,也有宗教片段,也有理論性的東西,也有體育史、數學、物理史,還有現狀,甚至包括政治話語,而且政治話語各種矛盾,還有經濟學。我在讀史書的一些片段,像曾國藩的日記,還有外國人對康熙的印象啊等等,還有包括嚴復在最早翻譯的使用的英語的疑問,還有《資治通鑒》里面在談到“云”這個詞的時候,還有我寫的過程中電視里面正在播放的東西,還有音樂。甚至有美容史。美容史其實是幾個我不認識的人在QQ里面互相在談論美容。關于美容我完全不懂,但是我把他鑲嵌到我的關于金三胖的胖瘦的問題里。關于這個胖瘦的問題是來自于我跟賈樟柯和余華、蘇童在1999年的一次聊天。當時蘇童剛從北韓回來,我問蘇童:你對北韓的看法是什么。他說:我的最強烈的感受是整個北韓全是瘦子,不用減肥,只有一個胖子,就金三胖。這里面的醫學的調侃和嚴肅以及我個人化的東西,把它放進詩歌以后,會發現非常有意思。然后把他跟減肥的美學作為一個帝國主義的話語,就像一個調侃和酸楚在里面,然后還有化學變化等等。

活動現場
諸如此類的嵌入以后,這一段完全沒有關系的原生態的語言,我沒有添加一個字,一段大概六七行的美容的片段嵌在里面,天衣無縫。而且這一段沒有辦法用聲音讀出來,我又做了消聲處理,所以我的這首詩里面充滿了聲音美學。我們以前關于聲音美學在當代詩歌寫作中的理解是不對的,是狹隘的。很多人覺得聲音就是美,就是音樂,就是音樂性,讀起來要優美,輕重啊韻律啊停頓啊等等。這些都是對的,但是只是從“美”的角度去理解聲音美學。我們都知道當代音樂不僅只是美,當代音樂里面包括了噪聲,包括對耳朵的折磨,包括了沉默。
像約翰·凱奇在音樂史上特別重要的一個作品叫做《4分33秒》,他在紐約演奏鋼琴曲,假裝要開始彈,把鋼琴蓋上擦擦臉,然后踩踩踏板,檢查一下,然后豎著耳朵聽聽觀眾中的咳嗽聲,讓大家不耐煩。從頭到尾一個音都沒碰,然后4分33秒的時候給大家鞠躬說:演奏完了。他認為在你們在期待這4分33秒的鋼琴作品演奏的過程中發出的所有的不是鋼琴的聲音,都是這首鋼琴曲的一部分。
這在當代音樂先鋒派當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作品。我的意思是說,音樂的聲音的形態學在我的這首詩里面有另外一種理解,有一種觀念的意識形態的文明意義上的一種嵌入和理解,所以包括消聲、包括聲音的材料、包括形態化都作為聲音的一種美學,嵌入和綜合到我的詩歌的寫作中去。而大家知道,所有的詩人都在處理一件事情,就是詩歌里聲音怎么轉換為意義,怎么轉化為時間的消失,怎么轉化為色彩,怎么轉化為情緒的節奏,怎么轉化為意象,一種內在,一種聽和不聽,一種容易觀看和看不見,所有這些轉換過程中,聲音已經變成一種時態學的東西。所有的詩人,我指的是我自己認可的有出息的真正的詩人,他們是這樣理解聲音的。
那么我在這首長詩里面是有很多激進的極端的實的驗,但是它融化在我的詩行的過渡銜接和串聯里面,所以最后我把兩百多種完全不同的材料嵌在里面,我個人認為是非常有意思的。但這首詩,我自己肯定,按照我們現在中國新人的寫法,按照我們眾多的讀者對詩歌的瘋狂,按照我們現在的學者,詩歌史的書寫者和建構者們、大學教師們,按照這首詩里出現的一切,這首詩都超出了現有的架構。相當于我們端著一個杯子,我們要喝一杯叫做詩歌的咖啡也好,酒也好,飲料也好,水也好,茶也好,但是我現在寫這首詩可能是一個池塘、一個水庫,一只杯子根本裝不下。這里面包含了大量事實的東西,包含了大量很難被理解,被透徹的理解的東西,所以它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被理解不被讀透,但是這沒關系的。
這首詩我更多的是寫給我自己,我作為一個讀者,由一個幽靈的“我”寫給一個活著的“我”的。200年以后,歐陽江河就從火星上被派過來。我這首詩集最后的篇章就是叫《火星人筆記》。我們中文是一個大的語言,我們的允許有些東西不會理解,不被讀透,這個不是對閱讀的不尊重,恰好是真正意義上的尊重。我覺得像我這樣的老頭子,61歲人了寫了一輩子的詩,也被認為是復雜詩歌的代表人物,要允許我寫的這樣的東西,這是我的一輩子奮斗以后的一個獎賞,一個特權。我和西川是耶魯大學在世界上最有名的一個復雜詩歌協會中唯二的中國會員。我當時進入這個協會是憑借這我的第一首詩《懸棺》。有一個耶魯大學的博士用四年的時間寫博士論文就是寫我的《懸棺》。而且他花兩年時間把它翻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他認為這既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所以認為它的母語不是中文,而最后被翻譯成英文以后也不是英文,是一種不知道什么語言的東西,只是在載體上是中文和英文,但在根本上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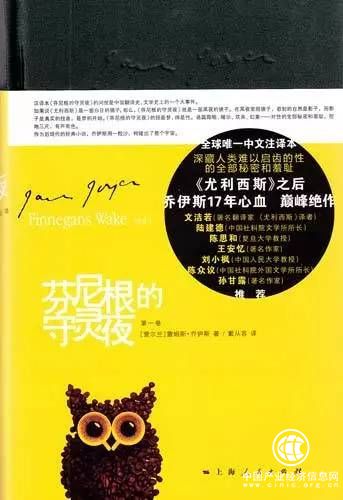
《芬尼根的守靈夜》又譯《芬尼根的覺醒》(《Finnegans Wake》)。喬伊斯更將他的意識流技巧和夢境式的風格發揮到了極致。這部小說徹底背離了傳統的小說情節和人物構造的方式,語言也具有明顯的含混和曖昧的風格。喬伊斯在書中編造了大量的詞語,潛藏了許多歷史和文化的背景以及哲學的意蘊,甚至大量運用雙關語。
就像詹姆斯·喬伊斯的《芬尼根的覺醒》,是至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被讀透的一本書。有一個100年的一個雜志叫《芬尼根通訊》在為這本書做引導和解釋。《芬尼根的覺醒》是一本用一百多種語言寫的一本書,包括中文。它的第一個字,這本書的第一個字是個復合詞,如果要把它翻譯成一個純粹的英文的話,得用3000到4000字再加以最簡單最淺顯的引導和解釋,才能理解那個字是什么意思和來源。為什么喬伊斯要這樣做,他的原意是什么?第一個字要花3000個字來解釋,我覺得詹姆斯·喬伊斯這家伙太是個混蛋了。他說了一句話,他說:我總得給那些無聊的沒事干的讀英語文學的博士們一點縫制博士帽的布料。這個家伙真夠狂妄的了,但是這真是一個偉大的人。我也給大家講我的這首詩里面至少有六七的地方起源于這本書的上半部。下半部至今還沒有出。說是一個上海一個女士一生都在翻譯這本書上。這本書的英文原文到現在還沒有,但居然純中文的翻譯已經有了,真是了不起。

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愛爾蘭作家、詩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作家之一,后現代文學的奠基者之一,其作品及“意識流”思想對世界文壇影響巨大。代表作《尤利西斯》,《芬尼根的守靈夜》。
今天講了這么多,我無非是要大家明白幾個事情。第一我講的長詩作為一種形態,他不是作為一種流體,也不是純粹作為一種固體的雕塑的東西,而是不同的轉換。而且它的聲音經常包含了消了聲的材料發出的聲音,比如說我們能讓一張桌子唱歌嗎?很難。但是我就是讓一個桌子唱歌了,就在這首詩里面。就是諸如此類的東西,希望大家理解。這是一個詩歌形態學的能力,盡管它里面包含了很多實驗性的、不完美的、走極端的東西,也包含了很多有靈性的東西,我覺得也沒問題,讓它存在就行了,大家也可以在里面找幾句自己喜歡的,我在里面也藏了一些很討喜的東西,悲劇喜劇正劇默劇都有。
甚至我在一個片段中還出現了庫克船長。大家都知道庫克船長是發現美洲大陸最重要的一個船長,海圖就是他發明的。其他人航海都是死了一半的人,他的船員從來沒死過,他有一整套辦法。他是一個現代航海的了不起的一個人,現代性開創者里面一定包含了庫克船長,這是我特別崇拜一個人。他認為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寫了幾個詩歌中的對句。對句相當于我們講七律的絕對,就比如說“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這樣得來全不費工夫,但是特別困難的對句。

詹姆斯·庫克(James Cook,1728.10.27-1779.2.14),人稱庫克船長(Captain Cook),是英國皇家海軍軍官、航海家、探險家和制圖師,他曾經三度奉命出海前往太平洋,帶領船員成為首批登陸澳洲東岸和夏威夷群島的歐洲人,也創下首次有歐洲船只環繞新西蘭航行的紀錄。
庫克船長的這幾個對句是寫在了他閱讀康德的《小邏輯》、《大邏輯》這個書的空白處,這些我都把他寫到我的長詩里面,好像看似毫無關系,但是其實真的是有關系。
現在這個時代和剛剛開創“現代性”的帝國時代不一樣。帝國主義時代的特征是擴張,以歐洲為中心出發,通過擴張到全世界才有殖民地,開拓才有美國。但是當代社會是收縮,從擴張往里收縮,所以才有當代物理和量子力學,越來越小,越來越微觀的一種世界觀,才有閱讀。剛才我在逛書店的時候,我在可以看到好幾個朋友,他們的名字已經從肉身變成一個收縮。比如電腦,世界越來越收縮了,但是電腦的病毒又在繁殖,非常有意思。我們是一個縮回來的時代,不是帝國主義的擴張的時代。我們向小、向個體化,向虛無的擴展,向收縮本身擴張,我們的擴張最終形成在我們詩歌的詩意的難懂的復雜性的深處,構成一個總的縮略而成的鉆石。美國一個保險公司的副總裁,一輩子沒有出過國的一個人叫史蒂文斯,他是一個偉大的玄學詩人。他說他在百萬顆鉆石中做出結果來。這個就是鉆石梳理。一個鉆石切成兩千個側面以后,對世界的不同層面的光的反射,這個構成了一個總的梳理。
版權及免責聲明:凡本網所屬版權作品,轉載時須獲得授權并注明來源“中國產業經濟信息網”,違者本網將保留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的權力。凡轉載文章,不代表本網觀點和立場。版權事宜請聯系:010-65363056。
延伸閱讀

版權所有:中國產業經濟信息網京ICP備11041399號-2京公網安備11010502003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