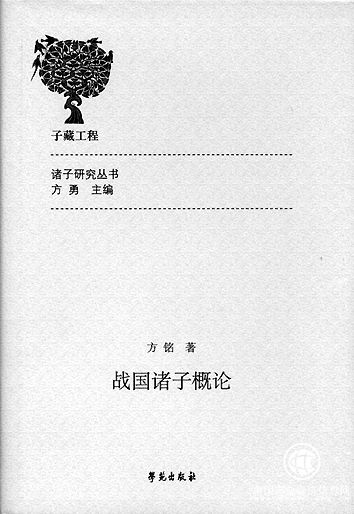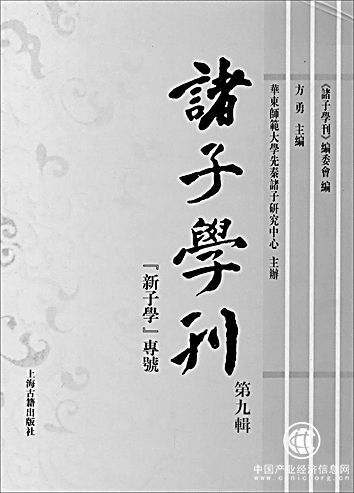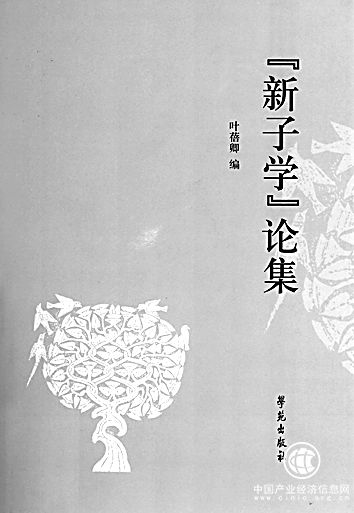“新子學”作為一種新的學術理念,自2012年提出后就引發了熱烈討論。近五年來,“新子學”在各方面取得了長足進展。2017年10月至11月間,在臺灣“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王俊彥主任的積極推動下,華東師范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方勇教授,連同數所高校的14位學者,在臺北展開了一系列“新子學”學術對話活動,包括臺灣“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舉辦的“第五屆‘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淡江大學中文系舉辦的“2017兩岸‘新子學’論壇”、“新子學”團隊與港臺“新儒家”名家及臺灣“中研院”經學研究名家的座談,以及臺灣“新莊子學”研究團隊與華東師范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在上海聯合舉辦的“海峽兩岸‘新子學’座談會”。參與此次系列學術活動的兩岸及海外學者共70余位,分別來自30多所高校,堪稱名家薈萃,這是“新子學”提出之后最大的一次學術對話活動。在此次兩岸“新子學”系列學術活動中,與會學者就“新子學”發展的重大問題展開建設性討論,在諸多問題上達成一致,也保持了相當的理論張力。
一
“新子學”認為,諸子學代表了中國思想文化原創時期的智慧,更具有經典性和生命力,是中國文化傳統中的關鍵組成部分。在研討中,有學者對此提出不同看法。淡江大學中文系曾昭旭教授認為,要在道統觀念下定位諸子學:“儒家的道統是內在的仁的血脈,經學就是人性普遍常道,也就是人性之善。要即事言理去呈現這個普遍常道,就是史。子部就是哲學,重在凸顯人生經驗中的理。集部就是文學,重在彰顯生活經驗中的感情。無論是即理以明道,即情以明道,還是即事以明道,都是呈現人性普遍常道的方式。由此可以點出子學的定位:它是即事明道中更需體現事中之理的、更偏向于哲學的方式。‘新子學’要有更嚴謹的概念思維,更準確的概念定位,更系統的理論性,這是‘新子學’何以為‘新’的定性所在。”
臺灣“中研院”林慶彰研究員認為,傳統文化中經學有其權威性,和戰國時期的“圣人集團”緊密相關,所論都是可垂教訓的道理。他認為:“《漢書·藝文志》里,經學和儒家是分開的,經學是六藝類,儒家是諸子類。可見在先秦,儒家和經學不大一樣。每個朝代有每個朝代的經學,要解決經學上的問題,就要回歸元典。”同時,林慶彰先生也肯定了諸子學的意義,他認為:“傳統經學、子學之間的隔閡可以打破,就是不要刻意去立異。經學、子學都是春秋戰國時期社會思想混亂的反映。假如把它們當作先秦時代的材料來看的話,雖然相互有出入,但是都奠基于當時的社會文化,《論語》《孟子》今天也可以看作是子書。”對于林先生“回歸元典”的說法,元智大學黃智明先生補充說:“經和子的關系,每個時代都有它的狀況,不必區分出誰高誰下,要回到經典上去理解。回歸元典,不是回歸經的神圣性,而是回到經典流傳前的面貌。”這種觀點和“新子學”有相近之處。臺灣“清華大學”楊儒賓教授、“政治大學”董金裕教授在討論中都認為,傳統經學歷史悠久,地位關鍵,影響深遠,子學也需要發揮自己的作用。
方勇教授認為,把諸子學界定為儒學、經學之下的學問,恰恰是舊觀念,有必要對此作深刻反省。他說:“有儒學學者提出儒學獨尊,諸子學在此理念下發展,‘新子學’要破除的就是這種觀念,要反對儒學獨尊,還諸子學以本來面貌,要重視傳統文化中復合多元的結構。”
二
“新子學”認為,在先秦時代存在著“子學現象”,在此之上有必要整合提煉出“子學精神”。對于如何綜論諸子學精神,楊祖漢教授認為:“儒家的道統被視為人生日常生活中的常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這些都是我們該義務做的。儒學講究常道、道統,‘新子學’似乎就不能再將道統當作指導原則,其指導原則要定在道家的思想上。道家所謂的道是以‘無’作為普遍的原則,‘無’便是去掉,剩下一個自然而然、空蕩蕩的、順應變化的生命。我認為這種普遍意義的道可以作為‘新子學’超越的指導原則。”淡江大學王邦雄教授認為,要把握諸子百家的整一性。他說:“今天我們講‘新子學’,是一家一家地講還是采用其他辦法?我認為可以按照《莊子·天下》篇的意思,讓諸子百家回到原來的神明圣王整體是一、道術整全的大傳統中去,這樣才能各得其所,走向文化的整合,創造美好的未來。”針對楊、王兩位先生的看法,臺灣“中山大學”賴錫三教授對“新子學”抱有更大的同情。他借助巴赫金的復調理論,描述一種文化主體內部就是眾聲喧嘩的多元復調的觀念。他認為:“《莊子·天下》篇是在肯定還是在否定思想多元?莊子的背后沒有怒者,沒有單一的概念,對語言、自我有一種批判性的反省。‘新子學’可以承認這種多元復調、眾生喧嘩的范式,因而齊物觀念可以成為‘新子學’的一個范式。”
三
“新子學”作為一個學術理念,首先意味著要探索一個新的諸子學研究范式。王俊彥先生認為,臺灣近幾十年來的學術一直偏向于西方的闡釋學,現在正在整體性地回歸中國傳統,而大陸“新子學”提出的重建諸子學傳統的主張,正好給大家提供非常重要的新視野,有助于豐富臺灣學界的研究。在此次研討中,中國傳媒大學刁生虎教授、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張耀博士,對“新子學”研究做了回顧總結,討論了有關“新子學”學術范式的若干思路。他們指出:“傳統思想研究關鍵是要回到原點,當代也正提供著回歸中國思想原點的極佳契機。身處現代語境中的當代研究者,不妨學習和繼承先秦時期的原創精神與恣縱氣勢,汲取元典智慧,融會當代理念,探索諸子學研究的新范式,以應對時代挑戰。”韓國圓光大學校教育大學院姜聲調副教授介紹了朝鮮半島前三國時代的諸子學。針對“新子學”的學術范式,臺灣大學林明照教授認為,“新子學”在子學研究中的“新”,包括新的材料(如出土材料、新整理文獻)、新的方法(如莊學研究中分析方法、跨文化方法)等等,這些都意味著子學研究的新方向。林先生也討論了“新子學”與跨文化研究的問題,認為無論是港臺“新儒家”還是“新子學”,面對東西方文化都有一種二分的預設,這種二分似乎會影響東西方文化之間的理解和對話,“新子學”作為對傳統學術范式的革新,這些固有觀念也是值得它去反思的。臺灣“中研院”方萬全研究員提到莊子研究中一個‘機會主義’的方法,即無論是概念的取得還是理論的使用,只要適合所要研究的對象,無論古今中外,都可以拿來運用。由此進行延伸,方萬全先生認為,子學最精彩的部分是它的哲學性,子學進行多元發展,這完全正確,但哲學絕對是子學優異性所在。對于上面提到的“新子學”研究中的路向問題,賴錫三教授則提出兩行的主張:“‘新子學’內部有很強的張力,一方面在回歸歷史脈絡,找回整體的原初語境;另一方面,我們回到兩千年傳統的歷史語境中,在叩問古典的時候,還是應以回應時代的處境為出發點。這就有兩種張力,到底是以回歸歷史為優先,還是以面對當下的處境為優先,要讓這兩者相互轉化。”在談到“新子學”的研究對象時,淡江大學殷善培教授從子學與四部的關系角度入手,談到“新子學”的研究對象、諸子與方技之別、經子之爭等問題。福建師范大學歐明俊教授則認為,“新子學”不能滿足于某一學科,不能滿足于就諸子學論諸子學,跨界會通才是“新子學”的創新之途。浙江科技學院張嵎教授認為,雜家是諸子學發展的必然,“新雜家”是“新子學”發展的一個方向。對于以上諸位學者對“新子學”研究范式的看法,方勇教授認為,首先,“新子學”作為一種新的學術建構,要注意一種整體語境,要從根源處思考,仍舊以“哲學”方式去研究諸子學,可能在很多根本問題上沒有辦法進行開拓。其次,在有關諸子學發展與現代學制建構的關系上,關鍵是不回避學科限制,在跨學科研究中找到出路,要注意研究的原理化和社會科學化。
四
在“新子學”如何面對西方學術這一點上,既存在研究方法問題,也存在文化立場問題。這其中的關鍵是借助發掘諸子學傳統,重構有關中國性的基本理解。關于此點,上海財經大學陳成吒先生認為,“新子學”作為全新的也是極為重要的觀念維度,對于當代國學觀念的建構非常關鍵。韓國江陵原州大學金白鉉教授認為,“新子學”不僅是中國的哲學,也是世界性的天下哲學,可以用來開辟二十一世紀的道路。臺灣“中研院”何乏筆(FabianHeubel)研究員強調要面對跨文化語境的挑戰。所謂“跨文化”就是能通古今中西之變,看到這四種文化元素在演變中的復雜交織,而這種情況和現代性結合,就涉及了所謂的“混雜現代化”,尤其是在中國等非歐美國家表現得更為典型。德國漢學家維托夫(ViatcheslavVetrov)認為,“新子學”作為一種中國文化認同的主張,同受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影響的當代學者立場并不相同,而是有其獨特的觀點,“自十九世紀早期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在全球化視野中討論自身的文化特質時,薩義德的東方主義始終發揮著重要的指導作用。然而非常吊詭的是,許多研究一方面非常依賴薩義德的理論,另一方面又嚴厲批判薩義德的理論。‘新子學’可以被視作‘漢學主義’的新選項”。針對以上不同看法,“新子學”認為,“新子學”對文化傳統有一個多元性的判斷,同時也不放棄對“中國性”的堅持。故而,“新子學”對內部文化資源來講是一個解放,而對外部文化資源,則意味著某種堅守。總之,“新子學”對于西方學術的態度是一種謹慎的開放態度,而根本上則致力于當代中國文化認同的建構。
五
對于傳統學術與當代社會的關系問題,與會的學者們有很多討論。東北師范大學張洪興教授認為,中國文化沒有所謂“劣根性”,“新子學”研究堅持以中國邏輯思考中國問題,以人為本,經世致用。在討論中,港臺“新儒家”學者強調以學術的方式面對社會,但并不直接介入社會,其所堅持的學術研究則以儒家思想化解現代人生問題為主線。而“新子學”主張,先秦諸子思想的關鍵不在“生命的學問”上,而在中國早期文明建構中的基本理路上,“新子學”的當代探索也在這里。有學者提出“港臺‘新儒家’缺乏公共領域思考”的問題,并認為“新子學”的關鍵是發掘諸子學中的治理思想,同時思考其在當代公共領域的價值。曾昭旭教授認為,不能撇開內圣來講外王,儒家的仁學并不是思考公共領域問題的障礙,反而是開出和接納公共領域問題的源頭。王邦雄教授反對“港臺‘新儒家’缺乏公共領域思考”的看法。他認為,要對港臺“新儒家”作同情的理解,港臺“新儒家”在西方文化沖擊之下,守護傳統文化之根,努力在學術思想上應對西方挑戰,并沒有放棄對公共領域的責任。他以自己為例,說明數十年來在民間講學的努力,是儒學介入現實的一種方式。王先生自己的諸子學研究,著力于由中國學術思考“新外王說”,他認為:“傳統思想的外王從孔孟、老莊到申韓,是一個客觀化的過程,不必依附西方來講。要講中學為體,中學為用,這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路。”對于學術與當代社會的關系,賴錫三教授則不同意混淆二者,他認為“新子學”是要回到諸子時代的范式,重新解讀中國文化保持其創造活力。“新子學”認為,傳統思想在文化上的功用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有必要提出對公共領域的新主張,這意味著要對諸子學的學術性質有一個新判斷。思考這個問題的關鍵,是重新理解中國文明體的基本構架形態。世界上除了中國之外還有很多不同的文明體,比如希臘、希伯來、印度等等,不同的文明體對文明早期構架的思路是不同的。要解決中國的文化認同問題,要找到多元文明中的位置,放在諸子時代的語境下可能會得到更好的解決。因而,對于傳統學術的當代使命,“新子學”持一種積極的開放態度。
六
在此次系列學術對話中,兩岸學者體現出的開通和善意,是基于對傳統文化的信心,對當代文化建設的熱忱。學者們都認識到,傳統文化研究既不能封閉自守,也不能以今釋古,而要在古典與現代之間作一種會通,為建構中國文化認同提供助力。王邦雄先生說:“我們有幾千年的傳統,不是文化沙漠,讓西方文化如入無人之境,我們不能接受。大陸已經崛起了,我們期待大陸在世界上擔當更重要的角色。”林慶彰先生也談到要肯定自己的文化傳統,他認為:“中國經典是世界特有的。外國沒有的我們都應該沒有,這個觀念造成很多混淆,使我們不能夠客觀地思考問題。”學者們都認為,“新子學”處在這樣一個時代,理應發揮更大的作用。方勇教授在研討中指出:“先秦諸子所屬的春秋戰國是天崩地裂的時代,而自晚清以來,我們在政治文化等各領域所經歷的動蕩與革新實則更甚于斯。縱觀數千年來世界文化與中國文化之發展,譬猶不同大陸板塊之間經由獨立漂移轉而互相碰撞沖擊,原先的矛盾只發生于板塊內部,新的矛盾則會從板塊內部擴張至板塊之間,由單一之個體超越至彼此之關聯。百年以來,中西文化之碰撞交流亦復如是。初始,西方文化及觀念伴隨著亂世之戰強勢進入中國,異質文明在引起震撼的同時,也給國人帶來了無所適從的茫然。時至今日,隨著我國政治經濟實力的不斷加強,我們已有能力也應該重新思考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大方向了。‘新子學’正是基于這一認識,試圖努力尋求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大方向,祈愿各家各派拋棄前嫌與門戶之見,一同投入到這場超越學術本身的偉大事業中來,為推進新一輪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宏偉事業共同努力!”
轉自:光明網
版權及免責聲明:凡本網所屬版權作品,轉載時須獲得授權并注明來源“中國產業經濟信息網”,違者本網將保留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的權力。凡轉載文章,不代表本網觀點和立場。版權事宜請聯系:010-65363056。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