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帙浩繁的古籍歷經歲月滄桑,記載著千百年來的中華文明故事。今年,是“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實施十五周年。十五年來,全國古籍保護狀況得到顯著改善,從漢文古籍到少數民族文字古籍,一大批珍貴古籍名錄公布,數千萬冊損毀程度不一的存世古籍得到有重點的分級保存和保護。
其中,經過“妙手書醫”——古籍修復師們的精心修復,更是讓數百萬葉破損瀕危的珍貴古籍得以“重見天日”,使千百年積淀的歷史和文化得以傳承。
正在國家典籍博物館展出的“妙手傳天祿 丹心鑒古今——國家圖書館藏清宮‘天祿琳瑯’修復項目成果展”,自開展以來吸引了大批觀眾前來參觀。展覽呈現了國家圖書館歷時8年完成的“天祿琳瑯”珍貴古籍修復項目,這是“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實施以來最大的一次針對國圖珍貴古籍的專項修復行動,300余冊一級破損“天祿琳瑯”藏書經修復師們的精心修復而重獲“新生”。《趙城金藏》、《永樂大典》、西夏文獻、敦煌遺書、“天祿琳瑯”珍籍……在有著古籍修復“國家隊”之稱的國家圖書館文獻修復組,一代代古籍修復師用指尖守護故紙里的文明,讓一件件國寶的原始風貌重新展現于世人面前。
古籍,是中華民族歷史記憶、思想智慧和知識體系的載體,以“天祿琳瑯”等為代表的經典古籍的重生,正在見證中華文脈的生生不息。
學古不泥古,“天祿琳瑯”歷經八年修復
修復難度超出預期,保證古籍安全和修復質量永遠被擺在第一位
“補天之手、貫虱之睛、靈慧虛和、心細如發。”這是明代周嘉胄在《裝潢志》里提出的裝裱良工應具備的本領。
今天的古籍修復師們依然恪守工匠精神,傳承著為古籍“續命”的傳統技藝。走進國家圖書館的古籍修復室,工作臺旁,埋首伏案的修復師們,手持各式修復工具,用最精準的老手藝在修復破損的古籍。每個看似輕盈的動作,都是修復師經過千百次練習后達到的精準與穩健。
“天祿琳瑯”是國家圖書館繼成功修復《趙城金藏》《永樂大典》、西夏文獻、敦煌遺書等珍貴文獻之后,又一次文物級別高、數量大的專項修復工程。
從古稀之年的國家級非遺傳人,到90后年輕修復師,國家圖書館文獻修復組幾乎投入了全部力量修復破損的“天祿琳瑯”,最終讓300多冊一級破損的珍貴古籍重獲“新生”。
不同于清代編修的大型叢書《四庫全書》,“天祿琳瑯”是清代宮廷善本特藏。乾隆九年(1744年),清高宗弘歷命內廷翰林院擇善本進呈御覽,列架收藏于乾清宮東側的昭仁殿,御筆親題匾聯,賜名“天祿琳瑯”,主要典藏宋、元、明刊本及影寫宋本等珍稀古籍。清嘉慶二年(1797年),乾清宮失火波及昭仁殿,“天祿琳瑯”付之一炬。嘉慶皇帝敕令重修昭仁殿,并命大臣重新甄選御花園與宮中各殿所藏珍籍,用7個月完成選目,重建“天祿琳瑯”藏書。
“天祿琳瑯”項目首席專家、國家圖書館古籍館資深修復師朱振彬介紹,2013年6月,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完成了“天祿琳瑯”未編書的編目并對其進行了破損情況調查。調查發現,館藏270余部3500余冊“天祿琳瑯”古籍中,約10%即300余冊存在嚴重的紙張糟朽、絮化、粘連、裝幀解體等問題,屬一級破損,急需搶救性修復。
朱振彬介紹,“天祿琳瑯”藏書年代跨度大,破損情況復雜、修復材料多樣,因此修復難度和挑戰是前所未有的。酸化、老化、霉蝕、粘連、蟲蛀、鼠嚙、絮化、撕裂、缺損、燼毀、線斷等破損問題在“天祿琳瑯”藏書中均有不同程度分布。“光是修復用紙的大類,就包括竹紙、皮紙、混料紙、宣紙、草紙等,并且這些紙還分不同的厚度、色澤、簾紋。修復用的絲織品,也包括絹、綾、錦、柞綢、絲線等。正是由于材質和其破損問題如此多樣,因此修復方案就不可能統一。在實際操作中,‘天祿琳瑯’每一冊書的修復,都是獨立案例。”朱振彬說。
古籍的“病癥”,每一種都不好對付。有些幾乎褶皺成一團的書葉,修復師們要耗費一整天甚至幾天來慢慢展平修復,哪怕一片小小的紙屑都要小心整理分析,努力歸位。為選擇修復紙張和實現染色效果,他們反復地討論、試驗,甚至嘗試遵循古法,嚴格按照中國傳統的手工造紙技術自己抄造紙張。
朱振彬介紹,《丹淵集》是整個修復項目里最難修的一本。拿到它時,它已經是“書磚”,粘連特別厲害,后來用濕揭的方式,用籠屜一點點蒸,光是揭開就用了十幾天。
“天祿琳瑯”修復中還遇到一個難題——大多藏書中都可見前人修復的痕跡,這些痕跡,是清除還是保留?比如《宋板班馬字類》1部3冊,修復前書葉表面褶皺不平,究其原因是前人修補時將襯紙整體當做修補蟲蛀的補紙,將書葉與襯紙通過蟲蛀處的糨糊黏合了起來。由于施漿處與未施漿處紙張力不同,導致書葉表面大量褶皺。修復專家反復評估后認為,修補的根本目的,是延長古籍自身壽命,這樣的前人操作痕跡不利于古籍保護,需要進行整改。
歷時8年,損毀嚴重的300余冊“天祿琳瑯”藏書終于修復完成。“開始預計的修復時間是4到5年,最終花了8年。這是因為修復難度超出預期,也是因為保證古籍安全和修復質量永遠被擺在第一位。圍繞‘整舊如舊’的修復原則形成了一個個更加具體、細化的課題,修復理念方面實現了新的突破,做到了‘學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朱振彬介紹說。
埋首故紙間,妙手補千年
年輕一代修復師,對工作有著內化成本能的熱愛,接續口傳心授的技藝,為古籍延續生命
國家圖書館現有古籍修復師22人,青年修復師占比超過70%。最近,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聯合國家圖書館開展的古籍保護公益項目取得新進展,敦煌遺書、頤和園“樣式雷”建筑圖檔以及一些傳世名碑拓片,正在他們的手中重現光彩。
青年修復師是古籍修復“國家隊”的年輕力量。他們盡管有著不同的求學背景、不同的專業興趣方向,但共同之處是對古籍修復工作都有著內化為本能的熱愛。
記者見到侯郁然時,她正在悉心修復一幅敦煌遺書的卷軸,手邊放著許多碎小的補紙,從她的每個動作中,都能看到“手藝人”特有的細心、耐心與嚴謹。她本科畢業于中央美術學院非物質文化遺產系,又按照自己的興趣,赴英國倫敦藝術大學攻讀紙制品修復專業碩士,2010年碩士畢業就加入了國家圖書館文獻修復組,做修復師的12年中,許多珍貴的古籍經她的雙手重獲新生。她印象最深刻的是2015年4月國家圖書館入藏的三件國寶級早期雕版印刷品。其中五代后唐天成二年(927)刻本《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一卷》,僅比咸通九年《金剛經》晚59年,為國內已知有紀年的最早雕版印刷品,彌補了中國作為雕版印刷術發明的故鄉卻無早期實物的遺憾。
侯郁然說,這件珍貴古籍屬于一級破損,古籍版本專家和修復專家共同商討修復方案后,決定對文獻用紙再造復制,為保證補紙顏色與佛經協調一致,還采用了古法植物染料對補紙進行染潢,最大限度地做到“修舊如舊,最小干預”。最終使般若妙諦,風采重光。
“書和書、紙和紙都有著很大區別。”侯郁然說,“修復工作中,當我見過的古籍類型越多,就越知道該使用什么方法來應對,不會再像開始時那樣‘發憷’了,這也是不停跟老師傅們學習的過程。”
而對于修復組的90后楊凡來說,對這份工作的熱愛可以讓她克服任何困難。楊凡2017年從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碩士畢業后加入了文獻修復組,在成為古籍修復師之前,她主要致力于不可移動文物保護的研究。
從做研究到做“手藝活”,這個自稱從小手工就不太好的女孩坦言“很有挑戰”。最初“學藝”時,她看著老師們拿著工具修古書,那工具就跟老師的手一樣精準可靠,可輪到自己,“就沒那么有感覺了”。
經過悉心的揣摩、無數次的練習后,她的雙手漸漸達到了精準與穩健。2020年,她參與修復的《祠堂畫像》在全國古籍修復技藝競賽上獲得了一等獎。她也對自己的動手能力更為自信了,“這門技藝的傳承靠書本知識是不夠的,需要在老師的帶領下,在實踐和練習中習得,現在我上手感覺更自信了。”楊凡說。
埋首故紙間,妙手補千年。年輕一代修復師,接續前輩們口傳心授的技藝,繼續與時間賽跑,為古籍延續生命。
全國古籍修復超385萬葉
全國圖書館系統古籍修復人才從十多年前的不足100人增至1000余人
國家圖書館早在京師圖書館時期,就配備了文獻修復人員。1949年至1965年,《趙城金藏》全面修復,讓殘破的國寶級珍貴文獻獲得新生,其后敦煌遺書、《永樂大典》、西夏文獻、“天祿琳瑯”陸續得到修復。
2007年1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意見》,在全國大力實施“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同年,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在國家圖書館掛牌。
國家古籍保護中心辦公室主任蘇品紅介紹,實施了15年的“中華古籍保護計劃”,是我國歷史上首次由國家主持開展的全國性古籍保護工程,對全國古籍情況進行全面深入的普查,并在此基礎上實現對古籍的分級管理、保護修復、整理出版、研究利用等。
“十多年前,我們在進行摸底時發現,全國圖書館系統的修復師不足100名,年齡多在40歲以上。當時的古籍工作,屬于各個圖書館比較邊緣化的工作,古籍保護力量也比較薄弱。自從‘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實施之后,這些局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蘇品紅介紹,由于古籍修復是一門手工技藝,因此在加強人才培養方面,盡量實行師帶徒、手把手的培養方式。
2010年,全國設立了12家國家級古籍修復中心。2013年6月,文化部委托國家圖書館成立了“國家圖書館古籍修復技藝傳習中心”,由國家級的非遺傳承人以“師帶徒”的形式傳習技藝,附設32家國家級古籍修復技藝傳習所。至今已累計舉辦古籍保護各類培訓班500余期,培訓學員超過2萬人次,覆蓋全國2000余家古籍收藏單位。此外,還通過與高校合作開設古籍保護相關專業,進行人才培養。
“在‘中華古籍保護計劃’整體的推動下,古籍修復的人才得到了成長,慢慢的新老交替,而且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做這項工作,所以我們沒有‘青黃不接’,不僅接上了,而且還接得比較好!”蘇品紅說,“在‘天祿琳瑯’的修復中也采用了‘師帶徒’模式,很多年輕修復師通過這個項目很快成長了起來,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收獲。”
如今,通過師徒傳承、在職培訓、高校教學的“三駕馬車”,全國圖書館系統古籍修復人才從十多年前的不足100人增至1000余人,年輕人成為主力,半數擁有本科、碩士或博士學位,形成了專業化高、創新力強、結構穩定的高素質古籍保護人才隊伍。
統計顯示,十余年來,依托12家國家級古籍修復中心,全國的古籍修復總量已超過385萬葉。
蘇品紅介紹,今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明確,要擴大古籍保護修復人才規模,提升古籍修復能力,加強瀕危古籍搶救性修復;制定古籍類文物定級標準,加強古籍類文物保護。“下一步,我們會推動將古籍定級標準納入文物定級標準體系,促進古籍保護與文物保護相融合。這樣,對于瀕危珍貴古籍文獻,就會更加注意去保護好它。”
書比人壽,“修書需要技術以外的知識”
修書就是盡最大努力延長古籍的壽命,讓我們古老的文明世代相傳
每個工作日上午,70歲的杜偉生都會出現在國家圖書館的古籍修復室,這已成為一種習慣。2012年退休之后,他被返聘回國家圖書館,除了繼續修復工作,還會指點年輕修復師。
杜偉生是古籍修復技藝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他經手修復的珍貴古籍,有敦煌遺書、《文苑英華》《永樂大典》、西夏文獻等,1991年至2002年的敦煌遺書修復項目就是在他主持下完成,他還曾赴大英圖書館修復整理敦煌遺書。
回憶起自己22歲從部隊退伍,被分配到國家圖書館的圖書修整組,從對古籍修復一無所知,到慢慢上手,杜偉生至今記憶猶新,“當時圖書修整組里只有我一個年輕人,師傅們都四五十歲以上,我的師父肖振邦、肖順華原先都是在琉璃廠做古籍修復,他們的手藝至少傳承了一百多年。我就跟著師父干,師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這一干就是48年。
修書久了,杜偉生被中國古人的智慧深深折服。“紙壽千年,敦煌遺書大多為唐朝時期,最早可以上溯到南北朝,保存1500多年了。敦煌遺書的韌性、強度非常好。唐代的紙一般是麻紙和皮紙,纖維比較純、氧化程度低、保存時間長。南北朝的紙比唐代的更好,紙漿的質量、抄紙的技術都比唐代要高。有的敦煌遺書里甚至會寫上用紙多少張,連半張紙也要注明,因為那時候紙是奢侈品,得到紙是不容易的事。從千年以前的古代用紙,能體會到中國古人的智慧。”
敦煌遺書修復之前,1987年,中國科學院研究員潘吉星先生來館里做講座,他從紙的纖維層面來研究分析敦煌遺書,這讓杜偉生受到極大的觸動。“古籍的紙本身就是文物。過去修書還會從古書上找合適的空白紙用來修書,現在的原則是只能添、不能往下拿。現在認為這些舊紙本身也是文物,所以我們修書用的補紙只能用仿制紙。”
1990年,他前往大英圖書館幫助修復敦煌遺書,在一件殘卷中揭出了一張非常珍貴的唐代“勑”。英國工作人員不知其意,當得知這相當于“王的旨意”后,他們大為驚喜。后來,大英圖書館“敦煌國際項目”所用Logo就是這張“勑”上的“勑”字。
明代周嘉胄在《裝潢志》中把書畫修復形容為“病篤延醫”,“醫善則隨手而起,醫不善隨劑而斃”。對于古籍來說,好的修復師如同“良醫”,杜偉生對此深以為然。
他認為,古籍修復“三分技術,七分經驗”,要想做好,更重要的是技術以外的知識。“修復師要懂紙,對傳統手工造紙要有了解,安徽的紙、浙江的紙、福建的紙,特性都不一樣,用來修書的紙不好找。幾千年下來,每個時代的書有每個時代的特點。”杜偉生說道,“古籍修復是交叉學科,牽扯到古籍版本學,還要懂化學、懂印刷史、造紙史、中國古代書籍史、文化史等等,每本書里面地域文化、地域美學,基礎常識要知道,才能在搶救修復古籍工作中得心應手。”
比起修書,技藝傳承和人才培養同樣重要。如今,杜偉生在國家圖書館有8個徒弟,還有40多個徒弟分布在全國各地。年輕一代修復師的學識和能力令他倍覺喜悅。“我的師父那一代,很懂版本學,不太懂古漢語。到我這輩能讀古漢語了,再到下一代年輕人,他們大都是研究生畢業,掌握技術之外的東西比我們這代人強多了。現在,顯微鏡能看到纖維、儀器能測定紙張厚度,修復也更加精準高效。新一代成長起來后肯定比過去強,這樣技術才能往前發展。”
這位專注古籍修復將近半世紀的“古籍醫生”,把賡續文脈看成人生大事,“古籍有修復周期,修過一次后,壽命再延續200年不成問題。老話講,古書‘百部存一’,今天講增強文化自信,留下來的珍貴古籍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修書就是盡最大努力延長古籍的壽命,讓我們古老的文明世代相傳。”
轉自:文匯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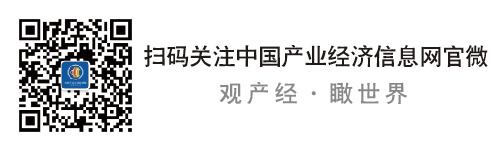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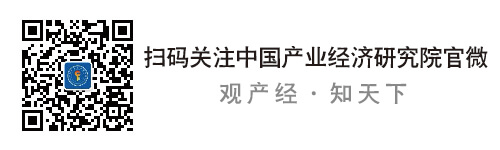
【版權及免責聲明】凡本網所屬版權作品,轉載時須獲得授權并注明來源“中國產業經濟信息網”,違者本網將保留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的權力。凡轉載文章及企業宣傳資訊,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觀點和立場。版權事宜請聯系:010-65363056。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