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城,感覺有些時日沒去了。而好好走蕩梅城的大壩,更覺得已是比較久遠的事了。
一
臘月的清晨,天色是那種略帶陰沉的灰白,宛如一塊浸過水的幕布,透出絲絲寒意。今天去梅城,心里頭那點期待,竟像個少年似的,撲騰著不肯安分。雖已年近花甲,可想起梅城,這顆心總還是溫熱的——這里安放過我六載求學光陰,十年工作歲月,后來又因著機緣,還主導過嚴州古城景區的經營。可以說,梅城于我,不是他鄉,是故園;不是風景,是眷念。

從七郎廟游船碼頭起步,這是我想好的路線。沿著自西向東的城墻大壩走,像是要親手撫摸一遍這古城的脈絡。碼頭還是那個碼頭,江水拍打石階的聲音,是一種沉厚的、不緊不慢的節奏。可抬眼望去,風景卻不同了。橋頭立起了雅高酒店,現代的建筑線條簡潔利落,窗戶玻璃映著天光水色。更遠處,跨江的高速公路橋與高鐵橋如兩條巨龍,并行著伸向天際。鋼鐵的骨架在鉛灰的天空下顯出冷峻的力度,帶著不容置疑的速度感。我站在這新舊交錯的時光里,一時有些恍惚。這是我熟悉的、又有些許陌生的梅城了。
沿大壩向東,不多時便來到定川樓。只見江面上幾艘大貨船緩緩駛過,拖出長長的水紋。這似曾相識的場景,把一段幾乎被歲月塵封的記憶,猛地撬開了口子,汩汩地涌上心頭——這里曾是老家麻車運沙船的卸貨之地,也是我少年時省船費的“秘密通道”。
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十二歲剛到嚴中,周末返鄉的兩角五分錢船費,對農村學子而言已是不小的負擔。我常與同鄉校友結伴,在那時簡陋而帶著斜坡的大壩上等候搭乘返空的運沙船。遇到心善的船主,會喚我們進船艙避風,艙內彌漫著濃烈的柴油味,卻能隔絕江風的刺骨。若是遇上陰臉的船主,我們便主動握起鐵鏟幫忙扒沙,粗糙的木柄磨得手心發紅,汗水浸濕了衣衫。船主看在眼里,緊繃的臉便會漸漸舒展,遞過一碗熱水,笑意里滿是淳樸的暖意。那些在船頭吹風的寒日,那些與沙礫為伴的午后,如今想來雖有酸澀,卻成了最珍貴的成長印記,也成為我生命河床底處,一塊溫潤的鵝卵石。
二
收起思緒,繼續前行。高大的澄清門城樓已然近身。這城門是古城的正門,也是古城的魂魄所在。我進門拾級而上,腳步在古老的木梯上發出空曠的回響。登臨城樓,視野豁然開朗,整座梅城仿佛一幅徐徐展開的淡彩水墨,盡收眼底。城內變化的確巨大,昔日低矮雜亂的屋舍,大多被修舊如舊的馬頭墻民居替代,青瓦粉墻,連綿成片,依稀可見當年嚴州府城的恢弘格局。老街巷弄蜿蜒其間,雖看不太真切,卻能想象那里該有酥脆焦香的嚴州烤餅,有玉帶河的水上婚禮表演,有街頭魔術與武術快閃,以及眾多游客的陣陣掌聲。新的生機,就生長在這古老的枝干之上,不顯突兀,反倒有種歷經滄桑后的從容氣度。

從澄清門下來,沿著城墻走,便到了福運樓一帶。這里江岸平緩,心也變得格外柔軟。就是這一段路,曾盛放了我人生中最平實也最美好的時光。那時我已在這城里工作、成家,也有了兒子。無數個傍晚,夕陽將江水染成金紅色,我便會牽著妻的手,看著剛會走路的兒子,搖搖晃晃地在前頭奔跑。他穿著小小的開襠褲,偶爾被路邊的野花吸引,蹲下來,用胖乎乎的手指去戳,隨即又站起來,發出“咯咯”的笑聲,那笑聲又清又亮,能濺到江里去似的。妻在后面溫柔地喚著“慢點,慢點”……。彼時,這一帶還是錢江航運公司客輪的碼頭,每當黃昏,便有悠長的汽笛聲“嗚——嗚——”地響起,穿透暮色,是歸家的信號,也是遠行的序曲。如今,汽笛聲已隨舊日的客輪一同隱入歷史,唯有江風依舊,拂過面頰時,竟還像是帶著當年那孩子笑聲的微溫,癢癢的,直鉆到心里去。
將近青云橋時,我正沉浸在這似水年華的追憶里,忽地,一片意想不到的絢爛,毫無預兆地撞進了眼簾。
是梅花!
就在江畔的泥地上,成片成林,豁然盛放。不是疏影橫斜的孤清,而是轟轟烈烈的爛漫。它們就那樣不管不顧地開著,粉的似霞,紅的像火,一團團、一簇簇,織成一片香雪海。萬千梅花在枝頭喧鬧著,仿佛把積蓄了一整個冬天的力氣,都化作了這傾情的綻放。它們開在古老的城墻根下,開在浩蕩的江水畔,開在這陰冷的臘月天氣里,是一種驚心動魄的美,一種敢于在肅殺中迸發生命熱度的美。
我幾乎是屏住呼吸走近的。就在這梅花深處,倚著江岸,有一座亭子,石碑上刻著“雙塔凌云”四個大字,是蘇步青先生的墨寶。亭子正好是個觀景的絕佳處。我佇立亭中,貪看著眼前的一切。說來也奇,方才還厚重如棉的云層,此刻竟像是被這梅花的精氣神所感,緩緩地、優雅地,裂開了一道罅隙。一束天光,金箭一般直射下來,不偏不倚,正正地落在這一片梅林與亭臺之上。剎那間,江水亮了,梅花亮了,連那古老的城墻磚石,也泛起了溫潤的光澤。整個世界,仿佛在一幅黑白水墨畫上,突然著了色,活了,醒了。
三
借著天光,極目遠眺,江山形勝,一覽無余。眼前,正是史稱“丁字水”的三江口。新安江自西而來,清碧如玉帶;蘭江從南注入,水色略深;兩江在此交匯,浩蕩成富春江,迤邐東去,直奔錢塘。江面開闊,水勢湯湯。對岸,南峰塔秀挺如筆,直指蒼穹,據說塔頂的那株黃連木,樹齡已逾二百載,與古塔一同呼吸著晨昏,堪稱奇觀。目光北移,巍巍烏龍山如一道巨大的屏風,橫亙在天際,山頂積雪未融,在云隙透下的光里,閃著清冷的銀輝。而左岸山巒的北峰塔,與南峰塔遙遙相對,拱衛著這千年府城。那塔下,曾是當年方臘起義的點將臺所在。想那豪杰當年,在此擂鼓聚將,指點江山,該是何等的意氣風發!這一南一北雙塔,鎖住這滾滾三江,藏風聚氣,成就了梅城千古不變的風水格局。

就在這壯闊的景色里,對著這傲雪的梅花,另一段關于我父親的記憶,悄然浮上心頭。我讀初二那年,家里來了兩位客人,穿著樸素的中山裝,舉止談吐卻頗儒雅。他們緊緊握著父親那雙滿是老繭與裂口的手,連聲說:“鄭師傅,謝謝您,真是太感謝您了!”原來,那時政府要修繕北峰塔,需要一批高質量的仿古青磚,每塊須重二十四斤,對土質、沙粒比例、窯火溫度要求近乎苛刻。家父是方圓幾十里最有名的土窯匠人,一輩子跟泥巴火窯打交道。他接了這活兒,從選泥,制坯,到火色掌控和封窯時機,他像對待新生兒一樣精心。終于,一窯高品質的“二十四斤磚”燒成了,塔得以順利修繕。父親后來對我們說,修塔是積德的事,磚要燒得過硬,才對得起天地良心。此刻,我望著云霧繚繞的北峰塔,仿佛能看到父親當年蹲在窯火前那專注的、被火光映紅的臉龐。那塔磚里,有家父的汗水與匠心;那巍峨的塔影里,又何嘗沒有如家父這般無數普通工匠的沉默堅守?他們或許未曾讀過多少書,卻用最質樸的方式,參與著歷史的書寫。這傲雪的梅,這凌云塔,這千年城,不也正是靠著這份拙誠的、堅韌的精神,才穿越風霜,屹立至今么?
帶著滿心的豐盈與慨嘆,我離開江畔梅林,信步走入城東的龍山書院。書院靜極了,庭階寂寂。這里曾是范仲淹任睦州(嚴州前身)知州時興學重教之地。站在其塑像前,似乎還能聽到千年前的瑯瑯書聲,感受到那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胸襟氣象。而嚴州這地方,又與那位“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的嚴子陵有著不解之緣。范公的濟世情懷,嚴子陵的高潔風骨,如同這土地深處奔涌的兩股精神泉源,一兼濟,一獨善,共同滋養了嚴州大地上醇厚而清剛的人文氣質。這氣質,化在歷代賢官的治理中,化在文人墨客的詩文里,也化在普通百姓如我父親那般“燒好每一塊磚”的勞作中。
步出書院,我忽然深切地感到,這座千年古城,從未老去。它像一株深冬的老梅,根須緊緊抓住歷史的巖層,枝干歷經風霜雨雪而愈發蒼勁,卻在每一個屬于它的季節,迸發出驚艷的新蕊。那是一種深植于傳統、又坦然面向未來的生命力。
此行訪“梅”,訪的是記憶中的故城,也是風雪中綻放的生機。梅城與梅花,在這冬日里,完成了一次意義深長的互證。它們告訴我,最美的綻放,往往源于最深的積淀。這便是我冬日訪梅所得——一份足以溫暖整個余冬的慰藉與希望。(作者:鄭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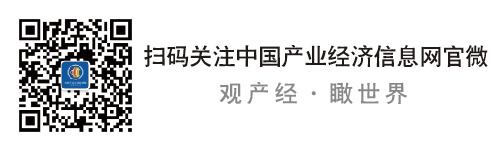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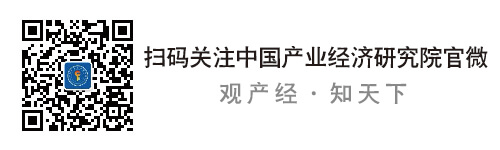
【版權及免責聲明】凡本網所屬版權作品,轉載時須獲得授權并注明來源“中國產業經濟信息網”,違者本網將保留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的權力。凡轉載文章及企業宣傳資訊,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觀點和立場。版權事宜請聯系:010-65363056。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