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那么一陣子,我們煞有介事地討論起“文學是否會走向死亡”的話題,甚至有人開始為純文學的未來敲響喪鐘。然而,有“人”怎么能沒有文學呢?文學本來就是生活“釀”出來的美酒,例如《詩經》,例如《羅摩衍那》,例如《荷馬史詩》……所以,盡管思想界、批評界在那里“憂天”,創作界的文學主題早已開拓創新,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追問和書寫悄然興起,使得“我們是否還需要純文學”的質疑不攻自破。這讓筆者想起美國學者約瑟夫·米克在《生存的喜劇》中所指出的:文學創作是人類一個重要特征,“它就應該被小心而誠實地檢查以發現它對于人類行為和物質環境的影響即決定它在人類的生存和幸福中起什么樣的作用,以及它能夠對我們與其他物種以及我們與周圍世界的關系提供一種什么樣的洞察力。”很多時候,“無為”的文學也總是“有為”的,否則我們今天回望人類歷史,該是多么令人心悸的荒蕪。而在全球化、城市化不斷加劇推進的今天,人與自然的關系一次次成為人類文明發展中的焦點問題,生態文學的功能理應得到更多關注。
以自然書寫的審美倫理超越現實秩序
2013年11月,筆者的生態文學研究專著《中國當代小說的生態批判》即將結筆時,在一片“楓紅杉黃”的黃昏勝景,我沉浸于“日暮的卷軸里”,大自然無邊的溫柔祥和讓人忘記了外部世界的“宏大敘事”:城市貫通天地的噪音,城鎮化強力擴張中被吞噬掉的鄉村,不斷向田園推進的沙丘……于是謅了一首像詩的東西,題為“自然的恩崇”權當后記,想象如果有來生,就做一棵“嫁與秋光”的樹——這,就是所謂自然療愈吧。
延伸大自然的觸手,那些擁有自然取向的書籍同樣有這種神奇的療愈功能。2019年,譯林出版社推出美國自然文學家艾文·威·蒂爾“美國山川風物四季”的新譯本,即厚厚的四卷本《春滿北國》《夏游記趣》《秋葉拾零》《冬日漫游》,這無疑是作者向美國自然書寫鼻祖梭羅的致敬之作。跟隨寫作者歡快的腳步徜徉在美國北部的春野,我們看到灌木林開滿了白色的山茱萸花,棉尾兔蹦蹦跳跳地鉆出了綠意蔥蘢的草坡,不由得想起了作家張煒的《九月寓言》里的“野地”:“瘋長的茅草葛藤絞扭在灌木棵上,風一吹,落地日頭一烤,像燃起騰騰的火。滿地野物吱吱唰唰奔來奔去,青生生的漿果氣味刺鼻……”在“夏游”之旅,作者闖進了蘇里斯河的大河套地區,看到了由于人類弄巧成拙的大開發造成的湖岸日益后退的事實,這讓我們記起楊志軍的小說《大湖斷裂》,當年的邊地農墾大潮,引發了湖泊觸目驚心的生態退化:湖水沉降,湖底裸露,湖面斷裂;作者游歷了俄亥俄的秋原,由林肯公路進入了曾經的“世界蜂蜜中心”德爾弗斯,在那里逗留時,我們的腦海中可能會閃現電影《蜂蜜之地》,那個能和蜂后“制定協議”卻無法阻止人類貪婪的無助女人,打動了多少人心;漫游在冬日曠野,仰望著翱翔天空的雄鷹,看到“機械文明的發達、人口的增加、環境的改變、DDT和其他有毒噴霧劑的廣泛使用、筑巢繁殖地帶的毀壞”等種種因素對于鳥類生存的威脅,這讓我們聯想到杜光輝的《哦,我的可可西里》里藏羚羊的命運,也想起姜戎的《狼圖騰》里那些被屠殺的小狼和天鵝,還有陳應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里那只傷痛欲絕的豹子……當然,閱讀者更多時候感受到的,是大自然四季嬗變的雄奇偉力和自我保育的美好,在與山川風物的交流中獲得至上審美體驗。
無論是抒寫對大地靜默的贊美,還是彰揚對荒原野性的敬畏,抑或感嘆自然對心靈的溫情救助,逃離城市、撤離浮華、逃避喧囂是自古以來文人雅士的一種人文意趣,也是文學的審美倫理超越現實秩序的表現之一。但是,生態文學的功能僅僅是為了用文字塑造一處“桃花源”,讓我們流連其中借以療愈精神的創傷?換言之,生態書寫只是世事紛紜里的一種心靈避難和救贖嗎?答案肯定是——不!而且我還想說:作家,請您走出桃花源吧,讓文字在現實的磨礪下更加鋒利。
在大地復魅中張揚生態公平
生態書寫的另一個本質功能,是在發展的視野下倡導環境正義,呼吁生態公平。這一方面意味著,在城鎮化的過程中,城市在制造“現代盛宴”之時,不應該以弱勢的鄉村里的生態問題為理所當然的代價;也意味著強勢文化必須對邊遠地區的生態多樣性、文化多元性保持足夠的尊重和保護。有時,“現代”所到之處,就像剪草機一樣,“修整”出一樣的城市、一樣的工廠和一樣匆匆忙忙的人群,鄉村和邊地的處境陷入尷尬。然而,文學作為人學,正應呼喚人道悲憫,警醒人們在前行的途中不斷反顧,撿拾那些被匆促的步伐所甩丟的人文財富。
在不少文學作品中,我們讀到,現代單一化的經濟發展模式和文化霸權對多樣化生存或文化多元性是沉重傷害,前一類如張煒的《刺猬歌》《你在高原》。《刺猬歌》將故事發生地設置在一個有著百年傳奇的古老村鎮,那里“人人都與林中野物有一手”,文本敘事中歷史與傳奇交織、現實與神奇勾連,充滿生命魅性。而到今世,一個叫廖麥的讀書人,他的夢想就是和家人開一片荒地作為家園,過“晴耕雨讀”的簡約生活。但商業巨子唐童步步緊逼,最終把那片田園變成了冒臭氣的工廠,連其最摯愛的妻子和女兒也在誘惑面前都背棄了他……鄉土鄉村被“格式化”掉了。正如多年前葦岸所說的:“在神造的東西日益減少、人造的東西日益增添的今天,在蔑視一切的經濟的巨大步伐下,鳥巢與土地、植被、大氣、水,有著同一莫測的命運。在過去短暫的一二十年間,每個關注自然和熟知鄉村的人,都已親身感受或目睹了它們前所未有的滄海桑田性的變遷。”
后一類寫作如遲子建的《逝川》和《額爾古納河右岸》、薩娜的《達勒瑪的神樹》和《多布庫爾河》、阿來的《空山》和《云中記》,都揭示了邊地原始經濟和古老生存模式的式微。阿來對弱勢文化消亡的態度比較理性和審慎,在談到《空山》時他說:“文化不是一個單獨的問題,而是與政治經濟緊緊地糾結在一起。任何一個族群與國家,不像自然界中的花草,還可以在一些保護區中不受干擾地享有一個獨立生存與演化的空間,文化早已失去這種可能性了。基于這樣的認識,我不悲悼文化的消亡。但我希望對于這種消亡,就如人類對生命的死亡一樣,有一定的尊重與悲悼。”《云中記》里,大地震后,岷江畔的云中村變成一片廢墟,而且正好位于一座山巒的斷裂帶上,不定什么時候就會沉入江中,幸存下來的村民們只好外遷,在別人的語言里流浪。4年后,村里唯一的祭師阿巴覺得自己應該回村盡自己的責任,去安撫和陪伴那些游蕩在村莊廢墟里的亡靈、山上的祖先和山神,義無反顧地返回云中村。阿巴走遍村子的每個角落,寧靜安詳地承擔起一個祭師的本分,與傾圮的院落、墻頭上的馬鞍、瘋長的野草、游蕩的野鹿……敘說著心事,滿懷虔誠地念誦禱詞,為曾經護佑山村的山神獻祭,最終隨著垮下的村子一起沉入江底。
在這些作家筆下的生態文本中,“原鄉”意味著一種精神文化、一種習俗的傳承,由此成為多元文化差異中的隱喻或象征。所以,生態書寫的“大地復魅”正是為了給狂熱的現代性祛魅,讓人們面對自然開發時考慮到一些古老的文化遺存,讓弱勢文化、邊地文化、游牧文化、少數族群文化多一些選擇的機遇。
在綠色發展視野下彰顯批判的本質
生態書寫的第三個本質功能,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則是批判——無論是對人類中心主義還是對過度城市化、對科學主義至上論或者對文化霸權主義,抑或對欲望主義的批判等等,因此,筆者有意把生態書寫的這種自覺叫作“生態批判”。
有學者把生態主義視為對啟蒙主義的批判、對現代性的反思,而實際上隨著知識分子與現代性陷入共同的危機,傳統現代型知識分子的社會基礎正被摧毀,知識分子的階層分化加劇,生態主義思潮正成為“新啟蒙”運動的核心部分之一,筆者將之稱為“生態啟蒙”。德國學者烏爾希里·貝克曾指出,這種新啟蒙是“啟蒙的啟蒙,它將自己的利刃磨得更為鋒利,對第一次啟蒙的苛求與普遍主義進行鞭撻,并在這種意義上成為第二次啟蒙”。
在中國,20世紀90年代生態文學勃興期,出現了一大批優秀的生態報告文學,如黃宗英的《天空沒有云》、沙青的《綠色備忘錄》、陳桂棣的《淮河的警告》、徐剛的《中國風沙線》和《綠色宣言》等等。作為現實主義的杰作,這些紀實文本從不同角度和視域對當時中國日益加劇的環境破壞、生存危機進行了真實具體的記錄。近年來,也涌現出一批有影響的生態文學作品,摘取了一些重要的文學獎項,如哲夫的《世紀之癢——中國生態報告》《水土中國》、肖亦農的《毛烏素綠色傳奇》、李青松的《一種精神》、葉多多的《一個人的滇池保衛戰》等等,生態文學確實已成“中國文學的新生長點”。
張潔的小說《這一生太長了》和詹姆斯·卡梅隆執導的電影《阿凡達》同樣在思考人與自然到底該如何相處的難題。《這一生太長了》中,動物族類在人類的野蠻開墾和殘暴屠殺下節節敗退,那只無法帶領族群尋到容身之地的頭狼忍不住自問:“對堅守一份尊嚴來說,一生是不是太長了?”它決定放棄頭狼職責,找個僻靜處悄悄死去,其纖毫畢露、寂寞憂傷的心靈世界透出驚心的凄美和徹骨的悲涼——最后竟被一個瀕死之人用盡余力射死。而動物的追問,也許正該是人類的追問:我們對地球的索取“多少算夠”?
該小說可以算作一部寓言,揭示了人與自然分離的終極命運:孤獨與絕望。而享譽全球的科幻電影《阿凡達》中,狂妄的人類仰賴機械的發達抵達了潘多拉星球,準備掠奪那里的礦產……該片無疑是對人類欲望主義、科技至上的嚴厲批判。有意思的是,百年前的科學小說滿載著作者對先進科技的向往,如中國的科學小說家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譚》,寫新法螺先生對科學與世界的關系百思不解,又對中國的落后深深憂患,竟然暈厥而靈肉分離,靈魂化成強悍無匹的發光原動力飛臨中國上空,憂憤于看到的慵墮世界,化成火球墜落到一老翁炕上,二人展開了一場有關時空的對話。光、熱、力是這部小說塑造的三個主要意象,寄寓了當時中國人的未來向往。百年后的今天,我們再看劉慈欣、韓松們,科幻小說家充滿了對科技造成人類與自然隔離的迷茫和批判意識。
一旦現代性的工具化價值觀成為文明的鉗制,其對立面就會出現,人類意識到:我們對大自然的過分掠奪必將造成“回報遞減率”,這樣,潛在的一個公共知識領域逐漸形成并不斷擴大,這一力量正意圖從“生態平衡”出發為自然界包括全人類的每個“個體”爭取“更好的”生存權利和生存空間。
近些年,從國家管理層面到社會各界的生態意識都在加強,我們在對以往的反思中重新體認了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重要意義,一系列生態保護制度和法規在逐步推行,各種自然保護區被建立,越來越多的物種被列入保護名錄。僅2019年,全局性的大戰略就有:1月,農業農村部等三部委聯合發布《長江流域重點水域禁捕和建立補償制度實施方案》,明確規定從2020年開始,長江將全面進入10年休養生息期;9月,鄭州舉行“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正式提出“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這些都將大大推動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這既需要人的理性自覺,也仰仗自然對人的啟迪和恩寵。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如何倡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協調自然保護與經濟高速發展間的沖突,推動中國走好“綠色發展”與“可持續發展”之路,這不僅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課題,也是中國文學創作和批評的重要議題。有人說,“文學是弱者的偉業”,但是蘇珊·桑塔格好像有另一種說法:嚴肅的寫作和寫作者都具有“不死性”。文學是丈量一個時代良知和溫度的尺碼,它如烈烈火炬,能照耀著千帆歸航。尤其是,“以生態及開發建設為主題的生態文學,其價值必然超越文學”。(黃軼)
轉自:解放日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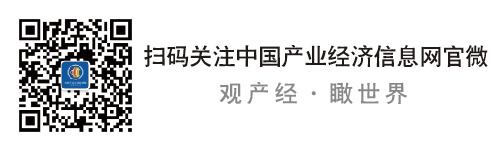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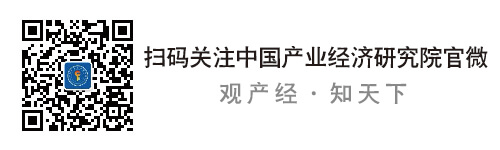
【版權及免責聲明】凡本網所屬版權作品,轉載時須獲得授權并注明來源“中國產業經濟信息網”,違者本網將保留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的權力。凡轉載文章及企業宣傳資訊,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觀點和立場。版權事宜請聯系:010-65367254。
延伸閱讀

版權所有:中國產業經濟信息網京ICP備11041399號-2京公網安備11010502035964